文娱动态
民情汹涌下的刑法扩张危险
日期:2011-07-01 作者:薛进展
薛进展,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从事刑法学教学研究20余年,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被聘任为上海市多家法院、检察院专家组成员。执业20余年,办理重大刑事案件数百起。曾被上海市律师协会授予“上海市优秀刑事辩护律师”荣誉称号。5月1日以来,能够在全国民众中对刑法产生强烈感知的莫过于醉酒驾驶的入罪,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将醉酒驾驶行为人抓捕到案,醉驾定罪判刑遍地开花。特别是随着知名度极高的“中国达人秀”评委之一的高晓松因醉酒驾驶被刑事拘留和被快速定罪判刑,醉酒驾驶构成犯罪的深度影响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醉酒驾驶入罪的过程中,民情酿造了醉酒驾驶入罪的刑法,刑法完成了一次从专家刑法到民众刑法的蜕变,民众更是从醉酒驾驶的入罪中进一步认识了刑法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醉酒驾驶行为的入罪,从客观角度看,将使人们的出行减少了来自醉酒驾驶的不安全感。虽然从5月1日醉酒驾驶入罪刑法规定生效以来,全国各地抓获了大量的醉酒驾驶犯罪的行为人,仅从5月1日至15日半个月的时间内,就查处醉驾2038起,其数量之多,堪称为同一时间段内案件爆发最为集中的犯罪类型。但是仅就该数据而言,已较去年同期下降35%,全国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而且可以相信,随着醉酒驾驶不断被以犯罪查处,醉酒驾驶的数量将呈明显的递减趋势。由于醉酒驾驶行为本身具有对公众出行安全的可能危险,而因醉酒驾驶的逐渐减少,社会公众的出行增加了稍许安全(因为只是减少了来自于醉酒驾驶的危险)。
从主观角度看,醉酒驾驶的入罪,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难以平衡的无限扩张的仇富心理。当今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有车的多少也能表明一定的经济实力,有名牌车辆的则更表明其不同于普通人的身价。因此社会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过程中,也催生了不少人的仇富心态。于是乎,只要与富有、官员、情妇等字眼结合,通过网络的无限传播,任何事件都可以迅即成为全国热点。与此相伴的恶意毁车事件也在不断充斥眼球。某个小区数十辆小车一夜之间被人恶意刻划的事件时有报道,小区停放的车辆被人从楼上恶意扔下的杂物砸坏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尽管醉酒驾驶的大多是普通型号的车辆,但名牌车辆的醉酒驾驶似乎成了醉酒驾驶的统一名称。人们对名牌车辆醉驾的不满心理已经积聚许久,当身着名牌,驾驶名车的人因为醉酒驾驶而犯罪被关押入狱,人们不平的心理至少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和谐社会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谐的基础或者在于物质享有的均衡或者是心理的满足,在物质方面难以保障均衡的前提下,通过心理的满足不失为一种和谐的有效途径。因此醉酒驾驶的入罪,更深层的意义可能就是通过心理满足而实现的社会和谐。
与以往的刑法修改所不同的是,醉酒驾驶入罪的立法,不是专家学者的智慧,而是民情汹涌的成果。也正是上述这些主客观的原因,在醉酒驾驶是否入罪的问题上,醉酒驾驶应当入罪的民意呼声极为强烈。而一些刑法学的专家们却在刑法的谦抑原则的指引之下,反对用刑法代替行政处罚,反对扩大犯罪的范围。在两种声音的争论之中,微弱的刑法学专家的声音无法盖过强大的民众声音,博弈的输赢也在声音的高低上决出胜负。
当醉酒驾驶入罪已成定论,醉酒驾驶行为已经实际被依法追究的时候,我们也应看到刑法的扩张趋势正在形成。
用刑法手段直接取代行政处罚手段,这可能是醉酒驾驶入罪最为引人注目之处,也是刑法扩张的集中表现。今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创设了包含醉酒驾驶在内的危险驾驶罪。为了与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这一刑法规定相衔接,4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同时,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刑法的增设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内容的删去,实际上是把原属道路交通安全法处罚的行为直接提升转变为刑事犯罪行为,用刑罚来处罚。行政违法行为直接转变为刑事犯罪行为,刑罚处罚直接替代行政处罚,这是刑法前所未有的立法创举。
应该看到,这种立法创举与刑法所固有的量变到质变的立法模式冲突。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设置,既强调犯罪的性质即罪质,也强调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即罪量,即所谓定性加定量的立法模式。此种立法模式通过罪量的控制将某类刑事犯罪的数量缩小在有限的范围内。如盗窃行为通过数额较大的入罪要求将绝大部分数额未达较大之数的盗窃行为排除在刑事犯罪的范围之外。但是在醉酒驾驶犯罪行为的法律设置中却改变了我国刑法所固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犯罪设置模式,将任何情况下的醉酒驾驶行为,不论其实际情况有何差别,也不论程度有何不同,一概纳入刑事犯罪的范围。由此在空旷无人的道路醉酒驾驶,醉酒驾驶仅行驶几十米远的路程,或者酒量甚好仅喝少量白酒的醉酒驾驶也都通通归入醉酒驾驶犯罪之中。
行政违法行为直接转变为刑事犯罪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凭空增加刑事犯罪的数量,扩大刑事犯罪的范围。如果以上述5月1日至5月15日半个月之内就查获2038件案件数为据,那么保守的估计全国每月将有约3000件醉酒驾驶案件的查获,那也就意味着全年就此新增30000余件刑事犯罪案件。如此数量的犯罪,在全部刑事犯罪中也将是为数甚多的案件类型。如此数量的犯罪,不是因为社会中存在危害较大行为而被以犯罪查处,完全是因为立法将行政违法行为转变为刑事犯罪行为,凭空产生的结果。也许这一数量在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30000余案件将牵涉到30000个家庭,牵涉到与此相关人的就业,牵涉到国家为查办犯罪启动刑事程序,执行刑罚而将要付出的巨额代价。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最高法院有关人员提出醉酒驾驶入罪要慎重,不是所有醉酒驾驶行为都应入罪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说醉酒驾驶的入罪导致刑事犯罪数量急剧增加还不足以担忧的话,那么更值得担忧的是,醉酒驾驶的入罪所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可能就是今后的交通管理和其他社会管理将更依赖于刑法。可以相信,醉酒驾驶的入罪,必然会使醉酒驾驶的人减少,人们出行的安全感一定程度上会得到提高。这种可见的效果,所引发的是全社会对刑法的过度依赖。可能的未来,醉酒驾驶入罪所产生的这种可见效果将作为一种成功的范例,成为人们呼吁将其他相关行为或者其他种类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刑事犯罪的范围,用刑事手段来加强管理社会的充分依据,例如将超速驾驶入罪、超载驾驶入罪、车辆安全保障设施不全的驾驶入罪、无证驾驶入罪等等。如此发展,可能有一天车辆或者行人乱闯红灯行为也将入罪。因为没有理由说这些行为比醉酒驾驶行为的危害小,刑事犯罪的范围由此也将进一步不断得到扩张。一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调控方法,比如民事方法、经济方法、行政方法和刑事方法,正是因为有着程度不同的调控手段和种类不同的调控方法,才能使社会的管理呈现为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刑法是社会各种调控方法的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调控方法无法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刑事手段。当一个社会刑事犯罪的范围极度扩张,允许刑事手段介入社会的方方面面,让刑事处罚无限延展,那么这个社会的恐怖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民意造就了醉酒驾驶的入罪,但醉酒驾驶入罪只能使公众出行减少了来自于醉酒驾驶带来的危险,而并不能排除所有出行安全的危险。除非把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所有违法行为都按照醉酒驾驶入罪模式全部照搬移植到刑法之中,公众的出行才能够得到安全保障。倘如真是如此,那么公众的出行将不是在交通法规的规制之下,而是在刑法的规制之下。当每个人的出行都在刑法的管控之下,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因此醉酒驾驶入罪只能成为刑法立法的特例,不应成为刑法扩张的范例和标杆。
团体组织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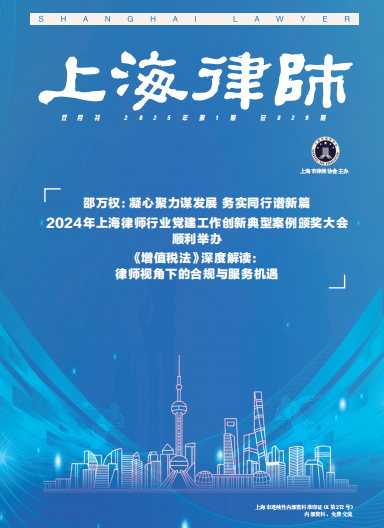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