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洪叔本 洪亮)子承父业——父子两代律师的心历路程
日期:2009-04-27 作者:洪叔本 洪亮
为纪念上海律师制度恢复30周年暨上海市律师协会恢复30年,作为上海父子两代律师,我们从各自的执业道路和感悟出发,从侧面反映上海律师制度恢复建立、发扬光大的历史进程。
父亲篇
我是上世纪68届高中毕业生,史称“老三届”。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口号声中,从小就想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了,我被分配到荒漠高远的大西北插队落户,不久被抽调到西北重镇兰州工作。若干年后,我返沪进了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回沪那年是一九八六年一月。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驱云见日,拨乱反正起,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紧缺。上海这座先进的城市,得风气之先,掀起了一股全民学文化的高潮,各级图书馆人满为患,门口排队候补的长龙随处可见,新华书店人来人往,公交车上看书、背单词的已成一道风景线,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辅导班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人人都有一种紧迫感,都想把浪费的十年补回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求知的欲望更加强烈。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了自学。恢复高考那几年,我还在大西北,由于环境恶劣,错过了机会,但我心中求知的欲望从来没有间断过,我看了很多书,做了很多笔记。国家成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有许多像我一样命运的人,无论他(她)多大年龄,无论干过什么,都选择了自学。
我选择的是法律专业。
律师制度从一九七九年恢复重建,到我回沪也不过六、七年,法律人才相当缺乏,以至于当年的华东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前身)每年在颁发自学高考毕业文凭时,不少企业等在校门口,极力招揽自学高考法律专业毕业生去他们单位工作。我的本职工作单位正处在合并阶段,拟成立集团公司,新领导也找我谈了话,如拿到律师证,将成立法律顾问室等,这是很诱人的,我看见了地平线上的曙光,自然要花十二分的力气来自学。虽已几近不惑之年,但雄心仍不亚于少年郎。我一边上班一边自学,除了上班,我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如鲁迅先生说的: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必须挤上时代的最后一班列车。
恢复建立律师制度,并不是一句空话。具体表现应当是大量法律人才的涌现,大批律师事务所的成立。上世纪八十年代,各级律师事务所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然而却缺少执业律师。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不难,各级司法局一路绿灯,只要有固定办公地址,三位有资格执业的律师即可。但是事务所成立了,律师却招不到,法律专业课程刚恢复,人才还在培养中。各级律师事务所为了留住潜在的律师人才,只要你自学高考有几门合格就可到事务所“实习”,我也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从此我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办案,终年忙得不亦乐乎。那时候,我们被称之为法律工作者。
为了不影响自学和办案,我本职工作很尽职,人际关系也处理得很融洽。每天除了上班,业余时间,包括休息天就跑去律师事务所,向有律师执业证的老律师学习办案,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不仅巩固了现有的理论知识,也学到了实际操作经验,学用结合,进步很快。自学是很艰苦的,而我用了三年时间顺利完成了法律专业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所有的课程,考试合格。
一九八九年我获得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自学考试毕业文凭。学以致用,为了成为一名律师,必须再接再厉,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取得律师资格,方可向律师的门槛跨进一大步。人们把律师资格全国统考比喻成“中国第一考”,可见难度之高,难于上蜀道。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是搏的时候了。”为了成功,我不得不请了几个月的事假,我没有了收入,不得不省吃俭用,我的妻子、儿子也不得不跟着我省吃俭用。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听辅班,做功课,背要点,析案例••••••我和几个同命运、共患难的未来律师,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不但总分合格,而且每门功课也合格。一九九0年我终于拿到了律师资格证书(被司法局保管了好几年未发),我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为我申请了执业证,墨绿色的兼职律师证。
当年律师事务所还占国家事业单位编制,而编制名额有限,无法人人申报专职律师。但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决定了律师事业要发展,律师队伍要壮大,不得已在特定社会情况下出现了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并存,这两只队伍人数不亚于专职律师,在特定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我作为兼职律师的一员,感到无上光荣,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里程中的一个特色。
在取得兼职律师执业证的当年,我参加了上海市第三期律师执业培训班,这是仅有的三期培训班,两年一次。1991年以后将律师资格统考每年举行一次。兼职律师,顾名思义,除了本职工作外,可以去律师事务所以律师名义对外办案。首先,我本职工作单位同意我担任兼职律师,其次律师事务所为我申请执业证,第三,我每年必须完成一定数量的办案记录,并准时参加培训。我的个人兴趣与国家需要完美结合起来。当年办案收费很低,但不无小补。我很高兴,为社会做一点儿有益的事,同时也使我从这一行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愉快。尤其办好一个案件,当事人很满意,千恩万谢,这时候心里特别高兴,特别舒服。我本职工作单位领导要我找几个科员,成立企业法律顾问室,大家分工负责为企业提供债权债务、商标专利、联营谈判等法律服务,搞得有声有色。我的兼职律师生涯持续到一九九七年底,上海律师制度进入最后改革阶段,所有国办律师事务所转制为合伙或合作所,所有兼职律师要不转为专职律师,要不取消兼职律师(高校兼职律师除外),特邀律师也得全部取消。
我在十字路口徘徊。社会上盛传律师如何如何大把赚钱,讲得神乎其神。这叫外行看热闹。大把大把赚钱的律师有吗?有,就那么几个尖子,可他们要付出何等艰苦的脑力劳动?他们将承担多少风险?外行人是不知道的。大部分律师由于环境、层次等客观原因,只能达到“温饱”阶段。甚而至于,没有案源,吃西北风。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将来老年的保障也须依靠自己努力赚取。所以从兼职律师转为专职律师,我足足考虑了两个月。最后,我还是选择从事了专职律师的工作,因为我爱上了律师职业,我已经离不开她了。
律师职业,令人羡慕。是自由职业里面比较有地位的职业。当你兢兢业业为当事人排忧解难,获得成功的时候,你会受到老百姓的尊重,同时你也能获得比较丰厚的收入,可谓名利双收。如果为人正直,品德高尚,承办的案件获得成功,你会觉得心情舒畅,凛然正气由此而生,律师职业可以体现你的人生价值,虽然你很平凡,办的案件也很平凡。十年兼职律师的执业生涯使我与她无法分手,我决定转制成为专职律师。
从一个法律门外汉到一个法律工作者,进而成为兼职律师,又在律师制度改革中转制成为专职律师。我是一个平凡的律师,办理了无数个平凡的案件,为无数个平凡的企业和个人担任法律顾问,我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崇尚“认真”两个字,无论什么样的案件,只要认真办理,就能获得意外的收获。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什么案件都办。经济案件,我能从一审败诉中找出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节:“8”系“3”篡改而来,从而认定一审系错案,在二审中要求笔迹鉴定,从而胜诉。刑事案件,我能几下现场仔细勘验环境,抓住一个细节,举一反三,为盗窃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护,最后检察机关撤回了控诉。我坚信我的一生没有虚度。现在我已经退休了,但还在发挥余热。欣慰的是我儿子接了我的班,他将在我原有基础上把律师事业向深度和广度推进。而立之年的律师制度,明天将更美好,更完善。
子承父业篇
九四年的夏天结束的很晚,直到九月,人们依然穿着短袖短裤。白天由于天热,路上行人很少,而我却顶着烈日。“同学,欢迎报到,这里是菁菁华政园。” “华政”,一所既古老又年轻的法学院,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我将与她相伴,并且相伴终身。
平安夜是我的生日,高三那年的生日,父亲送给我一个礼物,用纸包着,当我拆开包装纸,我看到的是一张简朴而质感的名片,我父亲的名片,上面印着“上海工贸经济律师事务所(上海功茂律师事务所前身)洪叔本律师”,名片的背面写着字“刻苦努力,儿自勉。1993年12月父字”。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我进入了政府部门。然而,单调的生活和不安分使我思考今后的人生。终于,鼓足勇气,在“衙门”度过一年之后,我将工作证交还了组织,那一霎那间,我有种解脱感,但似乎还带着一丝惆怅和迷茫。
一九九九年十月,在一举拿下律考后,我走进了一家陌生的律师事务所,没有让父亲介绍,因为,我已经长大了。直到现在,我并不认为我适合做律师,只是在众多行业里,我已经习惯了。
像大多数刚毕业的年轻律师一样,刚进所的我意气奋发,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前辈的认可,迅速学到做律师的技能和经验。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不管你在学校是怎样的风云,你现在什么都不是!从头开始,慢慢来。
由于事务所的老律师们都非常忙,很少能在所里碰到他们,偶尔他们会让我参与一个案件的部分工作,那也是极其难得的机会,因此,我倍加珍惜,力争做到尽善尽美。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件是我们主任代理一家企业起诉媒体失实报道,造成侵害其商誉的案件。由于资料繁多、证据复杂,在起草起诉状的过程中要将有关事实和理由,结合提交的证据表述清楚,在听完主任对案情的简单介绍后,我便埋头开始起草诉状。当我经过一整天的努力,在傍晚时分将诉状交给他修改时,我从主任紧皱的眉头中读出了些许信息,果然,我的心血被无情的扔了出来,只留下一句话:“重新理一下逻辑,抓紧改,晚上我要看!”顾不上吃饭,在奋斗数小时后,一份重新打印的诉状放到了主任面前。“内容还不够充实,分量不够,再改。”主任淡淡的一句话,使我原本由于饥饿而感到微微有些疼痛的胃收得更紧。当我再次把修改好的十八页诉状放在他面前时,听着慢慢翻阅文件的声音,坐在主任办公室外面的我心里很是紧张。“还凑活,明早八点打印好给当事人一份,听听他们的意见。”走在无人的街上,十二月的寒风灌进我的外套,我抬头看了看天空,深吸了一口气。低下头,手表显示:凌晨一点。
二00五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又回到了华政。“关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的地位是被告还是第三人,我个人认为……”在第四届亚洲企业论坛上我作着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主题发言,与会有来自日本、韩国、台湾、大陆的公司法学者近百位,大家济济一堂。此时的我,已经执业五年,专攻公司法,担任着华东政法大学公司法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亚太法律协会终身会员、上海市律师协会公司法研究会委员。
二00八年的最后一天,浦东国际机场,在美国取得法学硕士学位的我,回到了熟悉的上海,生我、哺育我、给我快乐、给我悲哀、更是给我希望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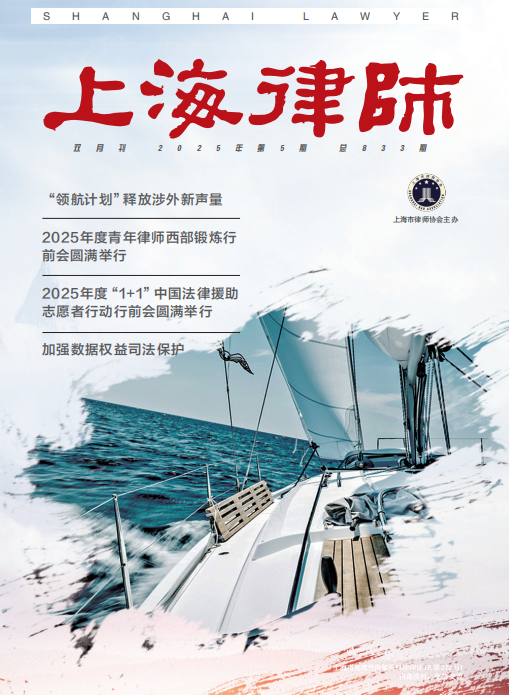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