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朱妙春)初涉版权——上海首例科技工具书版权纠纷
日期:2009-06-30 作者:朱妙春
案 由
原告沈雷与被告辛某均系上海某无线电厂的工程师。1981年6月,原电子工业部决定编写一部《中国集成电路大百科全书》(下称《大全》),中国电子器件总公司受命组织了《大全》编委会。被告辛某既是《大全》编委会成员,也是《大全•CMOS册》的编写人员。1982年底,辛某为减轻自己承编负担,加快编写速度,邀请原告沈雷参加编写。为此,辛某对编写小组人员和分工作了相应的调整,确定由沈雷编写第五章触发器、第九章CMOS双向模拟开关和CMOS数据选择器、第十章运算电路和第十三章第五节锁相环。之后,沈雷按期如数将承编稿件交给了辛某,但自1983年5月绍兴审稿会后,此事便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直至1986年5月下旬,沈雷从浙江医科大学某教师的求教信中才得知《大全•CMOS册》已在一年前出版。但是,该书在编写说明中,只将沈雷作为部分章节的材料提供者,而未列入编写人员的行列。同时,沈雷还发现由辛某承编的第十三章第六节CH259抄袭了自己发表在《电子技术应用》1983年第二期和第三期上的文章。于是,沈雷就向辛某、肖某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责任编辑王某交涉,却均告徒劳。在百般无奈情况之下,沈雷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987年2月,沈雷将诉状递进了卢湾区人民法院,主张署名权和财产权。立案后,卢湾区人民法院立即组成了合议庭审理此案。为追加被告,法官三上北京,两次延期审理,先后追加中国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和《集成电路大百科全书》主编肖某为共同被告。1988年7月4日,卢湾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宣判被告败诉。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一锤定音。然而,此案虽了,同厂工程师田某诉沈雷主编的《CMOS集成电路原理及应用》侵犯其著作权一案却仍在诉讼。此案沈雷一审胜诉,二审败诉。与此同时,还有田某诉《著作权连环纠纷的始末》一文作者王某和程某侵害其名誉权也在进行,此案田某一、二审均败诉。一时间,《大全•CMOS册》自身及其派生的案件达三起之多,真是一波多折,热闹非凡。
引 言
1986年7、8月间,与我既是同学、同仁,又是朋友的曹先生,要我与他一起接待一位叫沈雷的当事人,沈先生说他与同厂工程师辛某等人一起合作创作的作品《大全•CMOS册》被侵权,他在该书中既未被署合作者姓名,也未拿到稿酬,只是在书的后记中附带提到“上海某无线电厂工程师沈雷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章节资料”。沈雷是上海某无线电厂工程师,四十出头,满脸红光,一副学者派头,写得一手好字,令人肃然起敬,就是说话有些急躁。他说他先找侵权者去评理,如果要打官司就来找我们。到了1986年11月底,沈雷来找曹先生和我,说辛某与该书主编肖某相互推诿,谁也不愿负责任。辛某向他承认有错,并表示已向主编说明;而主编肖某则说,此事他知道,他不同意沈雷作为合作者参与编写,已叫辛某通知沈雷,辛知而不告是辛的事,因而此事与他无关。看来辛某、肖某相互推诿,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不告是不行了,于是沈雷便踏上了知识产权的维权大道。
认准被告 选择管辖
我和曹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沈雷的著作权被侵犯这是事实,并且被侵犯的权利涉及署名权和财产权。但是谁剥夺了沈雷的著作权,谁是本案侵权行为的主体呢?表面看来本案似乎是辛某过河拆桥,然后又瞒天过海,但仔细推敲又不难发现,辛某仅仅是一个编者,他没有这样的权力,要剥夺沈雷著作权的只能是编写小组、主编及编委会或者是组织这次编写工作的中国电子器件总公司。要在如此众多的主体中确定合适的被告,显然不大容易,而确定得正确与否,又会影响原告能否顺利诉讼。
我们对上述主体一一作了比较:(1)如果将中国电子器件总公司作为被告,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该公司已一分为三,即在电子工业部之下分为电子器件公司、微电子局和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大全•CMOS册》的版权归属尚未确定,因而也就难以确认谁是被告,且上海没有管辖权。(2)如果以《大全》编写委员会为被告那么很可能是捕风捉影,因为编委会并非经济实体,也非社团法人,而是一个在编后即散的临时机构,且到外地去诉讼,在当时也是不可取的。(3)再者,如果以编写小组为被告,该小组人员分散在上海、北京和江西等地,上海管辖也有问题,如果将他们作为被告,也将会给诉讼带来麻烦。(4)如果以主编为被告,也有难处,因为主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以主编个人作被告也觉欠妥。考虑再三,我们认为还是把辛某作为被告对原告最为有利。因为辛某就在上海,家住卢湾区,故卢湾区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且辛某有明显的侵权行为,特别是由他承编的第十三章第六节,其内容与沈雷于1983年发表在《电子技术运用》第2期和第3期上的文章基本一致,应属剽窃行为。再说稿酬问题通过辛可以追索,搞个水落石出。于是在1987年元月,沈雷便向辛某住地的卢湾区法院递交了诉状。诉状中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一、恢复原告署名权;二、追索被告侵吞的稿酬;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卢湾区法院根据《民法通则》中关于“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的规定,决定予以审理。这样,上海市首起科技工具书著作权一案便由卢湾区法院正式立案审理。
翻破案卷 认真调查
本案是《民法通则》于1987年1月1日生效实施后上海首起版权纠纷案,也是卢湾区法院审理的第一起知识产权案。因此,卢湾区法院对此案非常重视,承办法官也特别认真。审判长蓝关生是位资深法官,另外两位法官是年轻有为的顾建竹和严奇。他们对有关人员包括当事人、作品合作者、编写和编辑有关人员等一一作了谈话笔录和调查笔录,并三上北京,两赴国家版权局咨询商讨,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先后于1987年7月3日和1988年5月6日追加中国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和《大全》主编肖某为共同被告。同时为了使断案准确,卢湾区法院又请上海某无线电厂总工程师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对沈雷所写的《大全•CMOS册》部分章节和被告辛某所写的第十三章第六节CH259分别与其他编写人员修改后的稿件内容和沈雷于1983年在《电子技术运行》中所撰文章进行比较,作出《检查报告》和《鉴定报告》。法官们所做的大量工作,反映在卷宗里便是多达200多页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饱含了法官们的心血,具有大量客观真实的内容和对案件是非的评判以及法律的界定。当时,对我来说虽然办著作权案件是首起,但毕竟其他办案也有二、三年的经验,深知法院案卷的重要性。我和曹先生分工合作,在阅卷过程中摘录了许多重要材料,然后再细细咀嚼,慢慢推敲,了解了案情,掌握了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对案件的前景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那就是:
1.沈雷受辛某之邀,撰写了规定的稿件,即第五章触发器、第十章运算电路、第九章CMOS双向模拟开关和数据选择器以及第十三章第五节销相环,并通过辛某转交给肖某,用于《大全•CMOS册》中。不论如何评价沈雷作品之质量,譬如说沈雷所写之稿质量较差、文字较粗糙等等,均不能以此来抹杀《大全•CMOS册》采用了沈雷所撰写的部分章节这一重要事实。
2.国家版权局的工作人员对法官的二次咨询意见,明白无误地表明沈雷是作者,他对其所撰写的这部分内容享有版权。
(1)“版权所有者比民法中的法人、自然人范围要广些.。”
(2)“作品成为构成,写作人就是作者”。“沈雷写了几章,有先后顺序,有开头结局,有段落,有形式,肯定成为构件”。“构成每个章节就有作者的小版权,大小版权之间互不侵犯”。
(3)“原作品的原线条被抄袭,就是剽窃”。“沈雷是作者,如他认可修改的话,可确定他参与了某章的写作,可以不进编委会,但文章中要注明他是某部分的作者”。
3.上海某无线电厂总工程师叶柏海的《检查报告》和上海科技出版社的《鉴定报告》,也证明了辛某的第十三章第六节是剽窃了沈雷在《电子技术应用》中所发表的作品。
(1)叶柏海的《检查报告》指出“辛某在写此文时,起码来说是以沈雷同志的文章为主要基调而写成的。
(2)上海科技出版社鉴定时比照了340行,其中248行相同或基本相同,故鉴定结果是“70%基本相同(含完全相同)”。
对有关人员(包括当事人和证人)的调查,主要是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因为在阅卷后,还会有很多疑点和问题,这就需要去调查弄清。就本案来说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些是法官们认为与本案关系不大,而对于原告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证据,仍需要律师去取证。如关于沈雷创作的背景情况我就通过向当时的市仪表局副局长陆德纯(原十四厂厂长)和上海某无线电厂总工程师叶柏海等了解沈雷的技术背景和写作能力,并且均得到了肯定。
另外,对主编肖某,以及编写人员高某(后来退出)等也均进行了调查了解,得知沈雷写稿和被使用基本属实。
上述的阅卷和调查,使我基本上把握了案件的前景,从而为开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列出提纲 请教行家
在办案过程中,我不喜欢不懂装懂,因为开庭是最严峻的考试,不懂装懂是要出洋相的。因此,除了从阅卷和调查中不断掌握事实和知识,对于不明白之处则请教专家和行家。在此案的办理过程中,我选择了上海科技出版社作为重点咨询单位。一则专业对口,该出版社出版了许多科技工具书;二则《鉴定报告》是该社出具的,该社与本案多少有些关系。在去出版社前,我认真列出了近十个问题,如:1.何为资料?使用资料的程度?使用资料未经作者同意则如何?2.修改未经作者同意是否侵权?如侵权则对沈雷文章的修改是谁侵权?是电子器件公司?还是主编?3.编委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是组织机构还是编写机构?对《大全•CMOS册》是否拥有版权?4.中国器件总公司起用主编失职谁承担责任?是器件公司还是主编?5.编写说明不提沈雷提供稿件,而只提沈雷提供资料是否侵权?侵犯什么权?6.《鉴定报告》鉴定结果70%相同或基本相同,其基数是340行,为何不剔除不可比照的70行,以270行为基数?7.应用资料是公开的,是不是对公开的资料就可以抄袭?这种抄袭是否侵权?还有几个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我将上述问题列成提纲,尽管现在看来幼稚得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也确实是可以理解的。有一天上午,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踏进了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社长办公室,当我说明来意后,一位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男子站起身来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就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陈纪宁先生。陈主任又立即电话请来了俞大伟先生。陈、俞两人均十分好客,不仅对我提出的近十个问题一一解答,同时还拿来一本《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翻开来耐心地指给我看。 对我一时还不能理解的问题,他俩还不时举些例子,令我茅塞顿开。那天一谈就是半天,正是中午时分,就留我在他们食堂就餐。收获真不少,既有无形资产,又有有形资产;既有精神粮食,又有物质粮食。自那之后,我们交往频繁,我一有版权案件就去找他们商量,如后来经办的鲁迅稿酬案,汉语大词典署名权案,以及职业安全卫生百科全书版权案等。尽管在《眼病图谱》版权纠纷案中我们曾经一度代理双方,各为其主,但庭上争论不影响庭下的朋友之情。可以这么说,他们在版权知识上是我的启蒙老师,在工作上是我的同行挚友。虽然已时隔二十余年,但初次交谈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们给我的那本内部使用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我一直把它当作“圣经”一样地使用。《著作权法》实施后这本小册子我就珍藏起来,对这段友情我也十分珍惜,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归纳比较 后发制人
我的性格有些内向,遇事冷静思考,沉稳应对,故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表现在开庭时就是吃不准时不说,吃不透时少说,因此在庭审辩论第一轮时我往往观点不会和盘托出。然而到第二轮时,事实已基本清楚,双方观点也已基本明朗,此时我便捕捉争议焦点,寻找突破口,然后比较分析,讲深讲透,以期达到立论正确,言之有理,说理有序,论之有法,后发制人。在本案的辩论阶段我也是循着这个模式进行。而且本案有两位被告,共有四位律师。他们的第一轮发言长达两个小时左右,特别是辛某的首席律师董先生少年老成,临阵不慌,口如悬河。用他那圆润浑厚的男中音慢条斯礼而又抑扬顿挫地表述着自己的观点,给人一种立于不败之地的感觉。他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在下风官司中能有如此上乘表现的确实为数不多。如此冗长的发言,而且一个接着一个,实在是令人心焦和烦躁的。然而我却将坏事变好事,仔细地听着他们的发言,边听边思索,一边记下对方错误的观点,寻找对方错误观点的根源——对概念的混淆。一边迅速归纳出争议的焦点,成对列出一组组容易混淆的问题,以便在第二轮辩论时坦陈己见。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思索和寻找,我列出了九个需要分清的问题,如:第一,要分清共同被告和被告辛某;第二,要分清编委会成员和编写人员;第三,要分清作者和修改者;第四,要分清产品与作品;第五,要分清《产品说明书》和《双菱器件》;第六,要分清侵权开始和侵权结束;第七,要分清版权和专利权;第八,要分清整体版权和部分版权;第九,要分清个人邀请与参与编写。接着我便对所列的九个问题进行剖析和论述,指出被告代理人的狡辩和错误之处,真正起到了后发制人的作用,并达到了较好的庭审效果。双方辩论你来我往,共有好几轮,甚是激烈。直到下午5点30分,审判长蓝关生当机立断宣布法庭辩论结束,并宣布休庭20分钟。下午6时整,审判长将合议庭评议的结果当庭宣布:
一、责成被告《大全》编委会在下次翻印或再版该书时应当写明原告沈雷参加了第五章、第九章、第十章和第十三章第五节的编写。注明第十三章第六节的部分内容引自原告沈雷的有关文章;
二、《大全》编委会给付原告稿酬800元;
三、被告辛某除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外,还应承担经济责任,给付原告沈雷30元;
四、诉讼费30元和鉴定费40元由被告辛某承担。
感 言
2009年正值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三十周年,也是上海市律师协会恢复三十年。作为律师队伍的一名老兵,我自1983年以不惑之龄入门律师,至今亦有二十七个春秋了,其间历经案件逾千,其中不乏在业内影响较大的案子。然而,每当我回顾自己的律师生涯时,这个《大全• CMOS册》版权案总会浮现脑海。作为一名知识产权专业律师,该案是我踏入版权领域的第一步,是我知识产权律师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确立我的律师业务知识产权专业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而对此案我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的!
回忆起来,此案对我来说有两个难点:一是确定法律依据难。版权当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本案起诉时,《著作权法》尚未制定,《民法通则》也才刚刚实施,对著作权只作了简单的规定,除此之外,我们仅有一部文化部制定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可为依据,而这本条例还是内部掌握的。二是理解版权知识难。我接手本案时还是个版权领域的门外汉,对相关内容知之甚少,对版权案件更是陌生。因此初涉案情时,我根本就无从下手。如何使自己从门外汉变成版权律师呢?我的体会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则要重视敌人。
首先,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思想上要自信,不要怕。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斗志,才能勇往直前,冲锋陷阵。
其次,在工作方法上,要谦虚好学。不懂版权,就边干边学,在游泳中学游泳,在战争中学战争。在此案的办案过程中,我竭尽所能搜集与版权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为了把握案件前景,我反复研究案卷,几乎把卷宗都翻烂了。那些日子,我常常在妻儿入睡后挑灯夜读,直至天亮。我还虚心地向他人求教,以求正确理解概念、找准法律依据,这样我不仅很快地掌握了许多新鲜的版权知识,还因而结交了上海科技出版社办公室主任陈纪宁与国际部主任俞大伟两位朋友,真可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就这样,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又用学来的知识来指导实践,不仅赢得了这场官司,也使自己的版权诉讼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为日后代理其它版权案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在思想方法上,要勤于思考和善于思考。在办案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法律前沿问题,法无明文规定,如何办案?这对律师来说是一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律师不仅要勤于思考,而且还要善于思考问题,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第四,要善于总结和归纳,将实践中的经验拔高成理论,再用理论指导今后的实践,这样才有利于在短期内快速地提高和进步。我这些年已经养成一个工作习惯,每做完一个案子,我都会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整理成册,以指导今后的工作。例如在本案中,我就遇到了如何认定合作创作的问题,我将法官、对方律师和自己的观点与思路整理后,还写了一篇有关合作创作的文章。后来,在遇到“鲁迅稿酬”案、“八鸡宴”版权案、“眼病图谱”版权案等同类案件和同样问题时就了如指掌,应对自如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经过几个案子的艰苦历练,虽然有胜有负,但都让好学的我从中受益匪浅。待到后来,当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找到我时,我对处理版权案子已是游刃有余了,因此才能抓住机会,成功代理了鲁迅家族轰动一时的鲁迅稿酬案,从而在律师界和知识产权界崭露头角!
本案的另一个特殊意义还在于该案判决书开创了合作作品中合意与合创事实不必同步之先例,充分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从本案事实可见沈雷受辛某所邀既有合作创作的事实,也有合作创作的意愿。然而主编乃至黎某、吴某、朱某等合作编写人员均不同意沈雷进入编委会,更不同意其参加合作创作,也就是说只有合作创意的事实,而并无合作创作的意愿。然而,判决书不以有无合意为根据,而以有无合创的事实为根据。既然沈雷有合创之事实,那么也就理应认定其为合作作者。这一突破也就使本案对合作作品的认定,比较偏重以事实为依据的司法原则。这一原则就使本案有望成为合作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合意与合创可以分离不同步(即可以先意后创,也可以先创后意,或者边意边创)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司法突破,卢湾区法院与本案审判长蓝关生是功不可没的!在我撰写的《合作创作中的合意问题》一文中,我也表述了这一观点,从而为“《鲁迅两地书》是否合作作品”这一争论已久的话题提供了实例和理论。
该案代理的过程虽然比较艰苦,然而艰苦确能磨练一个人,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真是一次艰苦,一生受用。这点体会我想与刚刚踏进律师殿堂的年轻律师们共勉,请记住只有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才能取得成功,要相信坚持数年,必有成果,律师之路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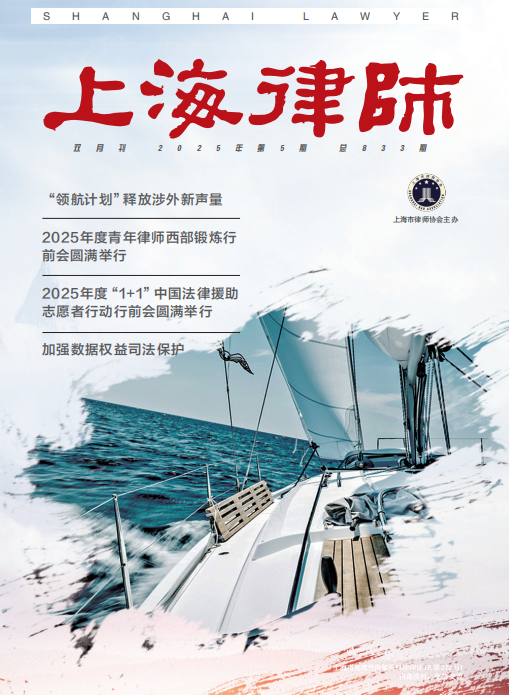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