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蟋蟀盆收藏杂谈
日期:2012-01-04 作者:汪智豪
每到夏末秋初,不少人喜欢玩虫,或买一只“叫哥哥”挂于堂上,虽居闹市,却仿佛身在瓜棚豆架之下;或置“唧铃子”于枕下,鸣声如乐,催人入梦;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养蟋蟀,斗蟋蟀。蟋蟀,又叫“蛐蛐”、“促织”,江南一带则叫“财积”。蟋蟀相斗,时间虽很短,但激烈,刺激,犹如人之拳击。因此不论老幼,皆大喜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玩家养蟋蟀,除了讲究蟋蟀本身的品种,蟋蟀盆也是非常考究的。蟋蟀盆,北方称为“蛐蛐罐儿”。其制作分为南北两派,北盆制作较为粗糙,形状单一,盆壁厚,花纹少;南盆则形状繁复,花纹精美。最早的蟋蟀盆都是由帝王指定的官窑烧制,作为贡品专供皇室使用,极少传至民间。官窑烧制的蟋蟀盆精致无比,种类纷繁。明宣德皇帝喜斗蟋蟀,苏州陆墓镇御窑村制作的蟋蟀盆也就成了当时的贡品。那里制作的蟋蟀盆,做工极为精致。远看形好,近看泥好,细看图好,翻开款好,内窥底好,敲之声好。至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都收藏了当时的珍品。我受家中长辈影响,从小喜欢捕捉、养斗蟋蟀。养蟋蟀和养鱼、养鸟一样,是中国民间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往小里说,是闲情逸致,往大里讲,也蕴涵了许多中国的传统哲学与文人理想。因为自己喜欢玩蟋蟀,就买了很多新制的蟋蟀盆,包括到苏州陆墓定制了许多名家盆,可是听到一些老玩家讲,要想把蟋蟀养好,光用新盆还不行,新盆有“火气”,用有些年份的“老盆”最好。由于地处上海,老南盆是上佳之选。
南式蟋蟀盆最早制作在南宋,高大深圆而厚,亦有方形,盖有平盖、坐盖、飞边盖等,底有平底、凹底。那时盆还有足,有三足、四足至六足。传至明代,盆式盆形更为精巧雅致,上面有花卉、百兽、山水、人物,盆底都有年号款和制作人印鉴。传世至今的老南盆基本都是明清两朝工匠所制作的。南盆的质地多样,有陶、瓷、玉、石、竹、木、漆雕器、戗金等等。每种材质的蟋蟀器具都有各自不同制式。有些流传有序,有些带有当地窑口风格,有些则是好事者随手而做。就目前存世的南式蟋蟀盆来说,陶土和瓷器的制式是联系最紧密的。而其他一些材质所流传下来的蟋蟀盆的造形可以说多种多样,并无一定的制式规格。从流传的物件来看陶土类和瓷器类的蟋蟀盆制式可以说是极其类似,特别是形状上,内无釉,盖式,底圈的做法都与泥盆类似。现存大部分为陶土类物件,瓷件极少见。玉质类的蟋蟀老盆极少但应为赏玩之物,而非实用,订置者应是玩斗蟋蟀的主。紫砂材质的蟋蟀用具,从流传下来的物件来看,规格复杂多样,方圆高矮都有。可见制作者多不按严格陶土类蟋蟀用具作为范本,也未只局限在宜兴本地窑口。我曾在安徽东源收到过带“宜兴紫砂”款的民国直同蟋蟀盆,只是感觉相对陶土类此物高度稍矮些,总体制式于常见的南式泥质蟋蟀盆还是很类似的。另苏博馆藏紫砂浮雕蟋蟀盆,此物制式特别,盖上多孔,有别于陶土类,可见制作者非识虫道者。石类、竹质、漆雕器、戗金蟋蟀盆,存世少,未见统一制式,多为好事者随手所做。明清两朝制盆高手为我们后人留下众多佳作。上海由于开阜较晚,所以上海本地先人留下的均为晚清民国的作品,苏州原产地因经历明清两朝更迭、太平天国战争等原因导致大量精美的蟋蟀盆毁于战火。再加上解放后破四旧等一系列原因,老蟋蟀盆的存世数量急剧减少,而安徽黄山市原为古徽州,旧时斗虫成风,素有男斗蟋蟀,女玩雀牌的传统。古徽州在明清两朝是全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士大夫和巨贾并出的福地。百姓们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当地斗蟋蟀的传统一直保持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逐渐淡去,那里留下了一大批好盆,所以皖南地区成为玩盆之人必去寻宝的地方。听老辈人讲上海七十年代末就有人跑徽州贩盆到上海赚取差价,集中在人民大道一带贩卖,而老南市区的文庙花鸟市场是徽州老盆到上海交易的主要市场。我去徽州收盆始于2004年,那时在好友的带领下,第一次到皖南的古村落走街串户收蟋蟀盆。当我看到当地农户从阁楼上、墙角边把一个个古老的蟋蟀盆搬到面前时,眼前仿佛又浮现出百年前白墙黑瓦的大宅院中徽州人品茶斗虫的那番闲情逸致。从那时起便一发不可收拾,每年总要到徽州去上四五次,并与当地一大批做古董生意的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当他们下乡“跑地皮”看到有好的蟋蟀盆都会及时电话联系我,帮我收下后等我有空的时候去取。这些年跑徽州收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累并快乐着”。
2009年的秋天,接到休宁古董贩子老詹的电话,说是山里有个农户家里有一个无款的鼓型盆,皮壳包浆一流,户家开价8000元已有当地好几个贩子看过都没谈成,问我是否有兴趣。我听完他的描述心中一动,无款的鼓型盆不就是典型的明代蟋蟀盆吗,真是有缘啊。适逢周末,我风尘仆仆地驱车赶到休宁,一顿丰盛的午餐后老詹带着我开车往山里赶,一路景色怡人,但我的心早已系在那个明代盆上面,再好的景色对我来说就是浮云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我们终于到了那个小村,老詹敲门入户后户主老先生一听我们是为了那个盆的事情来的,抬手就要请我们走,说来了几拨人了都谈不好价钱那个盆不卖了。我一听立马就急了,那时老詹赶紧掏出烟来用当地话和他商量起来,一番交流后老者终于不赶我们了,但坐下后他闭口不谈盆的事情。我仔细一打量他的家,就户主老先生在家,他的老爱人和儿子、媳妇都不在,从我几年跑徽州的经验来看有戏。于是我也开始和老人唠起家常,最后我把身份证掏出来给他看,说我从上海赶了六个多小时来看这个盆,并告诉他之前来看盆的所有贩子都是帮我收盆的,我是最终买家,价钱肯定是出得最好的。经过我的耐心劝说,老人终于答应给我看一眼盆,那是厅堂的时钟已经指向3点半。当老人小心翼翼从阁楼上把那个盆捧下来放在桌上的一刹那,我就断定那就是一个标准的明代蟋蟀盆。我强行压制住心中的那份激动,捧起盆仔细地看起来,那盆周身一层浓厚的包浆,盆身挺拔工手一流,历经400多年仍保存完好,实乃盆中精品。深吸一口气后开始和老人谈价,老人说是祖父留下来的,就剩这一个盆了,要的话就实价7000元。我一听就想立马掏钱,但是多年的收盆经验告诉我一定要还价,否则盆主会觉得你付钱太爽快怀疑漏价导致反悔不卖了。于是我就找了种种理由还了一个5000元,老詹也在边上帮着我还价,经过一番交流老人终于同意5000卖给我,当我掏出钱给他并准备拿盆时意外出现了,老人说怕收到假钱,坚持要到银行去交易,那时已经4点过了,农村的信用社都是4点半关门的。我当即给老詹使了个眼色,老詹就捧好那个盆起身到门口,等老人拿好存折慢慢带上门,我们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半。等我们来到信用社已经4点20了,等我把钱存到老人的存折上,他看到存折上打印的5000元存款满意地走出信用社时正好信用社也关门了。老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再回他家喝茶并留我们吃晚饭,老詹拽着我的衣服一边感谢一边往车子边上靠,拿着盆就直接上了车,我也只得和老人告别后上车走人。车子一走,老詹就说赶紧开,我问为什么,他说千万不能再去他家,4点半多了,他的老伴、儿子、媳妇都要回家了,一旦知道老人把东西卖给了我,肯定会横生枝节,说不定就把盆要回去了,所以一刻都不能停赶紧走。果然开到村口老詹就看到他的儿子在往家里走。回想起来真是好悬啊,一是来的时间巧,家中正好没人就老先生一人在家;二是交易的时间巧,再晚一会儿银行就关门了,交易也就无法完成;三是走的时间巧,没遇上家人反悔。晚上回到宾馆捧着温润如玉的明代古盆,心中的那份激动久久难以平抑。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每年我都会遇上好几次,家中每个精美的蟋蟀盆背后都有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样的淘宝经历使我乐此不疲。
当然,我在收盆过程中也留有很多遗憾。江苏南通也是各种精品蟋蟀盆辈出的福地。2008年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一批老蟋蟀盆的照片,我立刻就和盆主老王联系要去看盆,匆匆赶到南通,在南通老王家看到实物后我难抑心中的激动,当即就向他提出要收购,可是老王告诉我这是他父亲留下的东西暂时不想转让,看到我一片诚心,他便送了一个蟋蟀盆内的配件过笼给我。见老王如此,我也不便强求。当我准备告辞时,我看到他家博古架上摆放了许多紫砂的器件,我便与他攀谈起了紫砂,他倒是紫砂的大藏家,讲起紫砂如数家珍,谈到后来就讲到要是有个紫砂的蟋蟀盆就好了。真可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暗暗记在了心里。到了上海之后我多方寻觅终于在一老玩家手里高价收购到一个民国的紫砂蟋蟀盆,我再次联系了老王带上那个紫砂蟋蟀盆二赴南通,老王看到那个紫砂盆也是爱不释手,于是我便提出了与他换一个盆的想法,老王见我一片诚心便松了口,我就在他那些盆中挑了一个与紫砂盆价值相当的泥盆,再三道谢后回了上海。之后为了老王那些盆,我多次往返于南通与上海之间,虽然这一大批盆还在老王家中,使我留下了一份遗憾,但也由于这些盆与老王成为了好朋友,每次看到家中那个他换给我的盆我就会想起,在南通还有我的好友老王。
多年的收藏经历,其中的无限乐趣使我与蟋蟀盆结下了不解之缘,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更是那些寻盆的过程,每个盆后面那段故事更是我人生的一个个精彩片段,令人回味无穷。寻找蟋蟀盆的道路我将继续走下去,既是为了心中那份喜爱,更是为了人生那点执着。愿能有更多的收藏同好能与我交流收藏心得,品茗玩物共享美好人生。
(作者单位;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团体组织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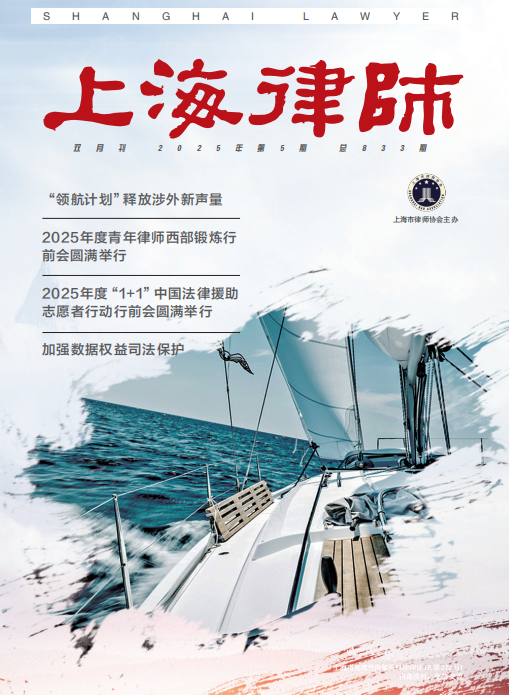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