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虐童案”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日期:2012-12-06 作者:傅平 徐建 何萍 姚建龙 麻国安 汤啸天 杨永明 丛洲 孙抱弘 李江英 杨峻
本期主持: 傅 平 上海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研究委员会主任、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新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嘉 宾: 徐 建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名誉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
何 萍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姚建龙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
麻国安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汤啸天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杨永明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丛 洲 上海市虹口区中小学法制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孙抱弘 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
李江英 上海市红十字会青少年工作部部长
杨 峻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权益部部长
文字整理: 蒋振伟
傅平:各位嘉宾下午好,近日浙江温岭某幼儿园发生教师对幼儿的虐待行为而导致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并对该教师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由此引发了社会各界对该事件的热议。今天,我们“法律咖吧”就围绕“虐童案”的定性、刑法是否应该增设“虐待儿童罪”、“虐童案”的成因以及相关的解决措施等四个问题展开讨论。
一、“虐童案”的定性
傅平:大家对浙江温岭“虐童案”的基本情况均已了解,那么虐童这一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如果是犯罪,它所涉及的是哪项罪名?在此,请各位嘉宾就“虐童案”的定性问题发表各自高见。
徐建:浙江温岭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来定罪,按照现有的材料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公安机关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在找不到一条非常准确、非常确切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下按照这么一条来定罪还是有一定依据的,相对于我们1979年之前用类推来解决问题,这个条文还不是完全的类推,这个条文中确实有这么规定,只是有些内容不完全能够非常的切题而已。检察院退回案件,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这种做法并无不妥,是完全合法的,反映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双方对于此案都有清醒的认识。
何萍: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来定罪是有欠缺的。如果严格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在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方面是有欠缺的,首先在客体方面,寻衅滋事罪是从流氓罪中分解而来,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的秩序,这个公共秩序可以从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生活准则,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方面来研究,但是“虐童案”它侵犯的客体针对的是孩子的身心健康,从客体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构成的。其次,从行为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与寻衅滋事罪比较吻合的一个行为方式是随意弄伤他人情节恶劣,如果扯耳朵也还算是一个殴打行为的话,那么其他的大量的行为,比如说把垃圾桶套在孩子的脑袋上,包括强迫孩子接吻,这种行为显然不能认定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因为这个情节比较恶劣,涉及的是一系列的行为,而且针对的对象可能比较多目前还无法查清。除此之外还有一项行为方式是恐吓行为,是刑法修正案新添加的一项内容,如果认为幼儿园老师是在恐吓小朋友,那么这一行为是否达到情节恶劣是有待探讨的。我认为如果完全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对于女教师的行为可以不定罪,可以通过行政处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对她进行惩罚以起到一个惩戒的效果。
姚建龙:“虐童案”是可以做无罪处理的。但是从一定要弄清一个罪名而言,我认为可以定寻衅滋事罪,但是要综合评价它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寻衅滋事罪有四种行为,其中一种是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毫无疑问,随意殴打未成年人是属于情节恶劣的一种,那么关键是看是不是符合随意殴打的标准,是不是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我认为完全符合。而它的主体和客观行为也是符合条件的,对于有人对客体方面存在的质疑,这个客体是双重客体,认为大家一直都把教室幼儿园当成公共场所,如上海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例中就明确规定幼儿园教室是公共场所,而且儿童本身就是一个公共产品。
二、刑法是否应该增设“虐待儿童罪”
傅平:目前,无论是舆论媒体、还是专家学者,都对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来定罪是否妥当存在很大的争议。造成这一争议的原因,在于严格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虐待儿童的行为与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是否符合。那么,是否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虐待儿童罪”,将虐待儿童的行为入罪量刑呢?
麻国安:不应该增设一个“虐待儿童罪”。如果要定“虐待儿童罪”首先行为要具有普遍性;其次是刑法的可处罚性,刑罚是最后的保障手段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要用刑罚,否则就会造成很多的行政执法权被刑罚权所取代,在行政处罚和刑罚之间还是需要有一段距离的。
姚建龙:应当单独增设一个“虐待儿童罪”。首先国际上对于虐待儿童有一个总体性的定义,包括五种情况,第一是身体上的伤害,第二是情感上的伤害,第三是性虐待,第四是忽视,忽视孩子成长当中情感上的需求,第五是剥削操纵童工行为。所以虐待儿童是一种综合性行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实体伤害,也不是一个单独的虐待行为,而是包括性虐待,身体伤害,精神上的伤害,忽视,也包括肉体的损害,这种伤害行为是非常综合性的,就浙江温岭虐童行为而言就包括了侮辱、猥亵等。其次,虐待儿童是一种静悄悄的犯罪,如果把它跟对成年人的虐待行为混在一起,会带来一连串问题。就虐待儿童而言,它的犯罪对象是幼童,是缺乏防卫能力、缺乏辨别能力以及缺乏救济能力的幼童,这跟老年人和妇女是不一样的,如果虐待行为把儿童和成年人合在一起,那么必然要做一个情节恶劣的特殊要求,这将会导致绝大多数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虐待儿童的行为仍然得不到刑法的制裁。
三、“虐童案”的成因
傅平:刚才我们从法律层面共同探讨了虐童行为的定性以及是否应当由刑法对虐童行为予以刑事处罚的问题,那么作为来自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第一线的各位嘉宾,是如何看待“虐童案”成因的呢?
汤啸天:“虐童案”不是一种孤立的事件,它的背后需要深思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不合格的管理问题,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已经下了六次整改的通知,但是这种机构依然存在,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眼开眼闭的执法”,也就是当地政府一方面开整改通知书或者勒令停办的通知书,一方面又还是让其生存。造成这样的原因是教育资源的欠缺,如果这样的幼儿园停办了,孩子入托就成了问题,太远的走不起,太贵的上不起,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社会在高速的前进,经济也有了号称第二大总量的飞跃,但是我们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是存在着一种短腿的现象,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地从顶层的制度设计加以解决,这种类似的问题还会大量的出现。如从“虐童案”一曝光出来,有相当一部分数量的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在从事着教师的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资源紧缺的问题,是一个资源紧缺的问题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需要之间的矛盾。
杨永明:法人不规范的操作,造成了这么一个失范的案例。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问题:第一社会问题,这些案子的发生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人口无序流动,造成地方政府原来所配置的教育资源不足。有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个是硬件不足,第二个是师资不足,这样就造成无资格幼儿园和无资质的老师的出现。第二家庭问题,家庭的迁徙流动主要是为了生存下去,所以家长把孩子享受怎么样的教育放在第二位或者第三位,甚至要求老师打孩子,只要不打残了就可以。其次是观念不对,认为幼儿园只是一间为孩子提供风刮不到雨淋不到,肚子饿不到,可以让自己放心赚钱的场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发现了虐童的事情,家长也很少去告学校,因为他们有求于学校,而且也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诉讼。第三教师资质问题,浙江温岭虐童案中的教师是没有教师资质的,她之所以能成为老师完全是因为和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欠缺有关,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教师本身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也没有接受过职业道德的训诫,再加上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幸造成情绪失控对现实的不满所以就找没有抵抗力的小孩发泄。第四舆论环境问题,一方面它有利于问题在阳光下解决,也有利于同行业的警觉,发现问题及早讨论及早写报告及早开会,但是舆论如果引导出了问题,那也可能是违法的,涉及到侵犯他人隐私权。第五后遗症问题,这件事不管是什么结果,后遗症客观上都已经存在,不管是对侵权人还是被侵权人,包括家长、幼儿园、地方政府实际上都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后遗症现象。
丛洲:我主要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看,认为“虐童案”的发生有两个主因和一个根源。第一个主因是学校教育的失败,我们的学校教育似乎仅仅是教孩子如何生存,学会如何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根本不注意教孩子做人做事的大前提,以至于越来越自利,考虑问题往往从自己的角度,越来越远离善良和公益。第二个主因是未保这个机制存在的问题,未保的工作一直以来都关注差生的转化,而对于孩子的基本权益包括健康权、人格权,平等权和平等地享受受教育权,这样的一些维权的事宜非常的漠视,导致学生投诉无门,解决问题无门。而对于根源问题,我认为是社会规则意识严重缺失导致的。守规则需要自上而下,但是我们这方面越来越缺失,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做老实人或者按规则办事,做老实人好像吃亏,成为了一种共识,以至于我们的学校时常会呈现一种畸形的教育形态,教师本来应该以身作则,但是好多学校教师教育孩子要遵守规则自己却毫无顾忌的不遵守。
孙抱弘:虐童事件是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所造成的,处于转型期之中有很多东西要转向现代,从理念、从思维方法、甚至从一些法律立法的角度都由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问题这样一个背景,从这个角度来讲浙江温岭虐童案其实是一个公共事件,不是一个个人品行的问题,问题在于我国的国民素质中非常缺少公共的意识、公共的素质,公共的道德,实际上虐童事件是违背公共秩序的,漠视了公共秩序,漠视了公共伦理的有关秩序,是用一个职业教师的岗位去虐待一个关于公共产品的孩子。
李江英:这个情况的出现体现了教育缺失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行政部门的问题,一个人的成长,整个教育机制体现在他的不同的年龄阶段包括在不同的行业上面,一个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成长肯定离不开各种各样层面的关心和照顾,尤其是社会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公德的教育、职业道德的教育如果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此类事件的发生。
四、“虐童案”相关的解决措施
傅平:通过刚才的讨论,我们对于“虐童案”发生的时代因素、社会因素、教育因素、家庭因素等均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虐童案”的发生可谓是“多因一果”。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最大限度地防止虐童行为,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汤啸天:将虐待罪的主体做一个扩大处理,不要把虐待罪仅仅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建议在虐待家庭成员后面加上或具有监管、照料看护责任的人,实施虐待行为情节严重的。如果负有监管、照料看护责任的人又实施了虐待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追究虐待罪的责任。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是一个少子化和高龄化的趋势,不仅有儿童的问题,也有老人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主体的扩大来解决。
徐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特定的时间段将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转移到幼儿园,使幼儿园老师可以起到父母亲的监护、保护、教育孩子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幼儿园老师相当于爸妈,幼儿园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家庭。我建议对于这个案子本身首先应该是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如果问题确实没有到达需要刑法来处理的程度,那么行政处罚或者其他一些处罚措施都可以进行,如果确实严重了可以用刑法处罚,但是关于怎么样适用刑法要有明确的界定。
何萍:刑法只是惩治犯罪的一种手段而已,对任何犯罪来讲预防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而且成本会更低一些,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效果会更好一些。社会的综合治理很重要,刑法的完善只是其中一个必要的方面,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事情是值得深思的。
杨峻:现在很多事情的发酵跟网络媒体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舆论的导向或者说媒体的导向,有时候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对于虐童案件中的两个当事人包括侵权人和被侵权人的权益的保护,媒体还是要有节制地报道,保护到当事人的利益,不侵犯其隐私权和人格权。
傅平: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作客“法律咖吧”,通过此前“头脑风暴”式的大讨论,让我们对“虐童案”的相关法律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上海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研究委员会作为以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己任的律协专业委员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密切关注“虐童案”的进一步发展,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作出新的贡献。谢谢大家!●
(本文内容根据录音整理,为嘉宾个人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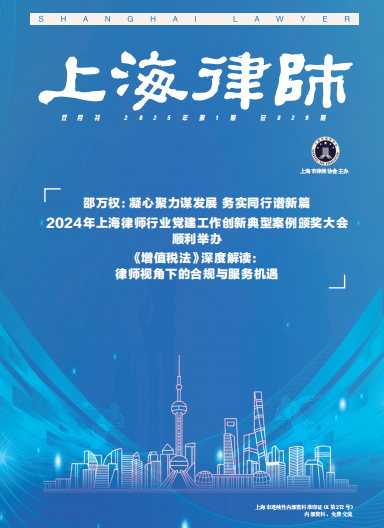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