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为了“得到”,须有“付出”
日期:2011-07-01 作者:王诗诣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细化了原有的法律规定,进一步表明我国现阶段对非法证据排除立法的价值取向。
然而,立法的进步并不能让人满意。1979年我国首部《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在长达30余年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严禁非法取证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从未停止;另一方面,由于非法取证产生的聂树斌、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层出不穷。有学者评论我国刑事诉讼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出现立法不断进步,实践裹足不前的怪象,更由此看淡《两个证据规定》的实践价值与发展前景。
其实,考察美国刑事司法的发展历程,其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并非“朝发夕至”,一气呵成,而是经历了相当一段有法不依,以及为了得到,付出更多的时期。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立法最早见于1789年的宪法第四修正案———“人民之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扣押,未经授权,不得侵犯,且除非依据由宣誓或代替宣誓证明之正当理由,并列明搜查的地点与所扣押之人或物品,则不得颁发拘捕扣押令状。”
然而在普通法国家,证据的相关性是证据的首要属性,也是审查判断证据的核心,正如英国Crompton J.大法官所言:“不管你如何取得证据,哪怕是偷来的,都与证据的可采性无关。”由于美国建国之初在司法层面全面继承普通法观点,因此该条一直未受到美国刑事司法的重视,直到将近200年后的马普诉俄亥俄州案(Mapp v. Ohio),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才终于一锤定音,正式将证据排除规则推行全国。
无令状搜查———州司法层面的广泛运用
1957年5月23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郊的警察局接到线报称一起爆炸案的嫌犯以及一些非法赌博工具可能藏匿于马普(Dollree Mapp)家中。三名警察前往马普家中试图进行搜查,但是马普拒绝他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住宅。随后两名警察返回警局并带了另几名警察前来支援。他们手中挥舞着一张所谓的“搜查令”并强行闯入马普家中。马普要求查看“搜查令”并乘机将其从警察手中夺过来藏进自己衣服里。随即,警察与马普发生肢体冲突并以“好斗”为由拘捕了马普。
在搜查中,警方既没有发现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也未发现赌博工具,但是他们却出乎意料地在马普床底的手提箱中发现了一些淫秽书刊。随后,马普因持有淫秽物品被逮捕并以此罪名起诉至地区法院。在庭审中,马普辩称她曾将这个手提箱租给一个寄宿的人,箱子里的东西并不属于她,但法庭依然采信警方所提交的证据。当马普的律师就搜查证问题质疑警方时,警方拒绝对其作出回应。最终马普被认定有罪,并被送往妇女管教所服刑。
同样的案情 不同的判决
一、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
马普被定罪之后,由于不服判决,她向俄亥俄州最高法院上诉。她的辩护律师再一次向最高法院阐述其观点:根据宪法修正案第四条,马普根本就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因为该案所有针对马普的实质性证据都来自不合法的搜查程序,这些证据理应被排除在法庭之外。
出乎意料的是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虽然采纳了辩护人的抗辩理由,却驳回了其诉讼请求。州最高法院认为该案中警方搜集证据所使用的手段确有“侵害公正”之嫌。但法院认为,从该案的取证过程来看,警方是通过平和的手段从某个场所获得相关证据的,在取证过程中警方并没有通过暴力手段从任何人身上搜出证据,因此这些证据虽然在取证过程中存在瑕疵,但仍应当认定那些材料的证据能力,并藉此驳回了马普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马普再次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1960年,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受理马普一案。最高法院审查的核心是:1、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否保证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在州司法层面加以运用?2、第四修正案所禁止的以不合理手段搜查的规定是否及于州司法?
经过审理,最高法院最终以6比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俄亥俄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作出有利于马普的判决。法庭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也应当适用于州层面,这意味着州法院不能依据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对某人定罪,这一判决也推翻了先前确立的沃尔夫规则(Wolf Rules)。
该案由克拉克大法官代表最高法院撰写审判意见。在说理部分克拉克大法官主要陈述了以下几点理由:
从维护宪法及国家法律体系稳定的角度看,他认为“摧毁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法不行。如果信件和私人文件能够被非法扣押,并用作有罪证据,那么第四修正案中所谓保护人民反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就没有价值,宪法也就无法得以实行。审理法院和其司法人员将罪犯绳之以法的努力固然值得称道,但是不能以牺牲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痛苦所确立的、包含在宪法中的基本原则为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努力。”
从各修正案条款间的关系看,正如Elkins案中最高法院审判意见所述:完善联邦体制的核心在于如何解决联邦法院间不必要的冲突。克拉克法官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Bill of Rights)赋予了第四修正案中“隐私权保护”(Protection of Right)以约束州司法的效力,这已经得到先例确认;因此,同样第四条中规定的“排除规定”也应当有约束州司法的效力。而州司法允许非法证据的使用实际上违背了他们本应遵守的联邦宪法。
从常理来看,克拉克法官认为“排除规定”是第四和第十四修正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根据先例推论而得的,更符合修正案本身的逻辑。如果不将“排除规定”适用于州层面,那么将造成荒谬的情况:在同一修正案的规范下,联邦检察官不可以使用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但一墙之隔的州检察官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
从司法实践来看,将“排除规定”适用于州层面更有利于杜绝“银盘理论”。所谓“银盘理论(silver platter doc-trine)”是指在西方国家,服务人员向被服务者传递钱物和账单时常用银盘托着,在证据法中则暗喻州警察向联邦警察传递非法证据。(该理论的具体内容见下文详述)
克拉克法官认为:如果违宪搜查的证据同时被州法院和联邦法院认定无效,那么上述的情况也很快会被消除。
州与联邦的博弈
州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迥异,其原因并非本案表面所显示那么简单。其实在马普案之前,证据排除规则就已经在联邦层面确立并运行了近半个世纪。在1914年威克思诉合众国案(weeks v. United States)中,戴大法官(Justices Day)指出:宪法第四修正案就像卫兵守卫城堡那样,保护着人民的住所免受政府的入侵,我们建立“排除规则”就是要让那些非法证据不能被用来指控被告人。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和州各有独立的司法体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也自然只在联邦层面有效。同时,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立法目是通过约束联邦政府的权力达到保护各州和人民的个人权利的目的。因此,正如威克思案判决中所述那样,“宪法第四修正案不是针对这些(州)警察的不适当行为而制定的”,因此,州警察也毋需受其约束。
在其后的发展中,一些州采纳了联邦的意见确立排除规则,另一些则认为该规则影响警方办案而拒绝采纳,由此带来了州与联邦的立法不统一,甚至给联邦警察规避证据排除规则带来便利。正如上文所述的“银盘理论”,政府在办理联邦案件时往往与州警察合作:先由州警察采取无令状搜查等手段搜集证据,再将证据移送给联邦警员,借此涤除这些证据在联邦司法体系中的污点。
这一做法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长期盛行,直到1960年埃尔金斯诉合众国案(Elkins v. united States),最高法院才首次根据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对州层面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给出意见。而马普案则是最高法院首次确认州刑事司法程序也应当受到宪法的监督以确保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保障。
并不完美的规则
经历了两个世纪发展的“排除规定”终于由马普案所确立,但几乎在最高法院法官落下法槌的同时,批评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因为警方的微小错误就将真实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并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并且让公众承担放纵罪犯的后果,不但影响警方乃至政府的公共形象更威胁到社会安全。正如沃伦法庭(Warren Court)所质疑的那样“排除规定在干扰警方工作方面也许‘走得太远’”。在1961年之后的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也屡次通过案例对 “排除规定”内涵外延做了各种修正。
一、善意之例外(Good Faith Exception)
善意之例外确立于1984年合众国诉里奥案(U.S.v.Leon)中。该案中,警方搜查所使用的令状存在瑕疵,并在庭审中被确认,但是警察在执行搜查任务时并不知道该令状有瑕疵。控辩双方由此引发争议:在搜查时搜查人员善意相信其所持之搜查令状有效,其搜查行为是否构成对宪法第四修正案之侵犯?
最高法院审理认为:即使后来证明令状有瑕疵,但警察当时是在相信搜查令状有效的心态下实施的搜查。因此可以认定,警察是在主观善意并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进行取证,排除规则并没有起到阻止非法行为的作用。宪法第四修正案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应一味排除该类证据。最后,最高法院肯定了检察官的主张,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定。
此后,善意之例外还进一步发展,延伸到了依据之后被认定违宪的法律所为之搜查取证行为。
二、必然发现之例外(inevitable discovery rule)
必然发现之例外确立于1984年尼克斯诉威廉姆斯案(Nix v. Williams)中。在该案的侦查中,警方已经将某关键物证的搜索范围确定并已经展开搜索,此时本案被告威廉姆斯向警方提供了该关键物证的具体位置,省去了警方劳师动众的搜查工作。在庭审中,辩方认为威廉姆斯做此供述是由于受到警方诱导,违背了米兰达规则,因此该证据应当被排除。
最高法院审查后认为:“证据排除规则”之目的在于通过排除证据进入法庭的手段,阻吓警察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在保障公民权利与放纵罪犯的风险的利弊权衡中,立法者选择了更高位阶的价值进行保护。但是,如果某证据即使不采用非法手段也必然要被发现,那又应另当别论———法庭即使采纳了上述证据,也不会使控方处于更有利地位。相反,如果直接排除这些证据,将不利于在“阻吓警察非法行为”与“使陪审团获得尽可能多的犯罪证据”这两种价值间找到平衡。
此外,“必然发现”之例外并不要求警方之善意。一方面,当警方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时,他们不可能预知要寻找的证据是否必然会被发现;另一方面,假设警方知道证据必然被发现,他们也不会进行任何有风险的取证活动,因为在此情况下,通过任何可疑的“捷径”来获得证据都将得不偿失。此外,法律也已经确立了一系列针对非法取证的制裁措施,如内部惩戒和民事责任等,这些措施也对警方取证进行心理约束,使 “必然发现”例外不致成为鼓励警方不当行为的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坚持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此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将远远超过以善意为条件所产生的阻吓效益。
“排除规定”与我国刑事诉讼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可谓百年磨一剑,直至今日,该制度仍在不断细化和发展。而考察其创立与发展,可以借石攻玉,为准确评价与健全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供思考空间。
我们固然应当认识到不容乐观的现状:我国的刑事诉讼的首要目标仍在从惩治犯罪向保障人权过度,法官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仍远远高于对程序正义的尊重,刑讯逼供是众人皆知的秘密,长期奉行的口供中心主义如影随形,似乎我国的刑事诉讼经过三十年的建设仍然千疮百孔不堪一击。但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都不应成为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失望的原因。正如《两个证据规定》中规定的: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与非法实物证据相对排除原则等,这些原则都是首次出现在我国立法中,这很好地诠释了我国刑事司法在推进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时的信心和决心。在实践中规范取证手段,保障人权这一刑事司法的终极目标,需要几代法律人持之以恒的努力,因此我们在指责的同时,更应当保有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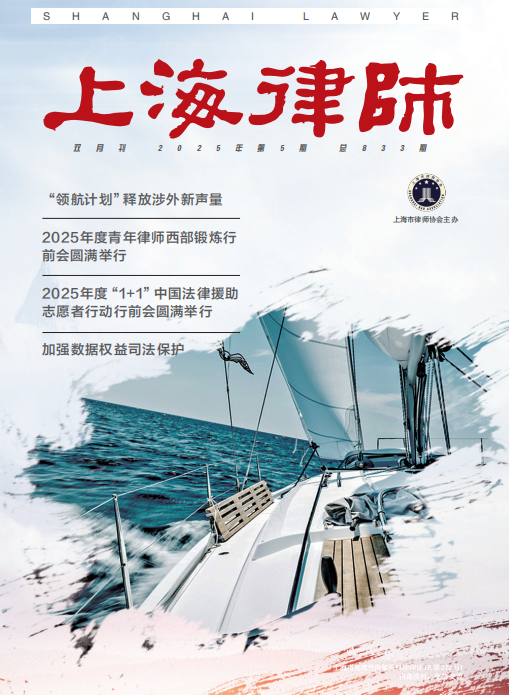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