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让法律的阳光照进“疯人院”
日期:2011-08-01 作者:卢意光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并公开征集意见。这部耗时二十几年,十次修改的法案,一经公布,立刻引来社会的广泛关注,“强制收治”即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前不久,武钢第二职工医院精神科的一名精神病患者徐武在该院强制收治4年多后,从精神病院逃走并来到广州,试图证明自己没有病,但在广州被武汉警方强行带走。由于徐武被强制收治的背景是与单位领导存在严重纠纷,多次举报及上访,所以,公众质疑徐武受到单位领导报复而“被精神病”;再者,徐武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武汉警方千里迢迢赴广州抓捕,涉嫌程序违法,于是,公众广泛质疑警方滥用公权力制造“被精神病”。
当然,在立法过程中,我们也听到有专家提出,“被精神病”只是个案,不足以成为精神卫生法关注的重点。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危险。一是该专家还没有意识到“被精神病”所带来的恶劣社会影响,以及对“被精神病”对象的严重伤害后果;二是我们从来没有统计过“被精神病”的数量以及严重程度,大家所了解的都是通过记者怀揣社会良知、舍弃个人安危、极其艰难取得线索和证据、并公之于众的报道。到底有多少“被精神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关注,谁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贸然认为“被精神病”仅仅是个案,不应成为立法关注的重点的言论难免让人感到怀疑,感到忧虑。
“被精神病”本质上是社会矛盾扭曲发展的结果,弱势一方斗争失败以后,被强势一方冠以“精神病”的帽子,关进与外界隔绝的精神病院,失去人身自由,既是惩罚,也有利于维护强势一方的胜利果实。如我们熟知的武汉徐武、南通朱金红、广州何锦荣、昆明段嘉禾、深圳邹宜均等等,都是“被精神病”的典型案例。当然,有人在犯罪以后,利用“被精神病”不被追究刑责的法律制度,想方设法成为精神病,从而实现逃脱法律制裁的目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本文不作论述。
科技发展到今天,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自身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对大脑精神活动的认识就更显捉襟见肘了。依据目前的医学水平,精神疾病有近400种,发病机理很复杂,目前发现的有3000多种原因,现有医学诊断仪器和方法还无法客观评估和准确判断精神病的患病程度,大多数指标依赖于人为的观察和与患者的交流询问来完成。所以,诊断或鉴定为精神病更多依赖的是医务人员或鉴定人员的职业经验和个人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务人员或鉴定人员受到外界压力或利益诱惑,“被精神病”的诊断风险就大大提高了。所以,如何解决“被精神病”这个严肃的命题,仅仅依赖于医学科技水平的提高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精神病诊断的客观诊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既然“被精神病”都是有原因的,“被精神病”的目的是让“患者”进入一个封闭、与外界隔绝的精神病院(俗称“疯人院”),由此,如果能够将精神病院变成一个开放的场所,让法律的阳光照进“疯人院”,从制度设计方面对“被精神病”进行预防、救济和惩戒,那么,“被精神病”问题也就不难解决,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对这些问题均有涉及。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第一、“被精神病”的预防。
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重点在精神病的诊断程序上。《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或者其监护人对非自愿住院医疗结论有异议的,可以选择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复诊。承担复诊的医疗机构应当在接到复诊要求后指派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复诊,并在5日内作出书面复诊结论。”“对复诊结论有异议、要求鉴定的,当事人或者其监护人应当自主委托依法取得资质的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医疗机构应当为当事人提供司法鉴定机构的名单和联系方式,并提供技术手段。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并在7日内完成鉴定。”
不难看出,“草案”对于初诊为精神病的患者,规定如有异议,可以申请复诊和鉴定,应该说考虑还是非常周到。
“草案”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还规定:“医疗机构应当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定期对非自愿住院患者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本人及其监护人;属于强制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的,还应当将评估结果向有关公安机关报告。除强制医疗的患者外,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可以在获知不需继续住院治疗的评估结果后立即办理出院手续。”这是治疗期间,对患者定期复查的规定。
可以看出,治疗期间,患者是否可以出院由收治医疗机构确定,如果对该医疗机构的诊断有异议,是否也可以申请复诊或鉴定呢?“草案”没有规定。
笔者估计,“草案”没有规定的原因可能是考虑节约医疗资源,避免因患者或监护人的异议反复复诊或鉴定,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是否可以建立异议审查制度,就是对于入院前存在社会矛盾的患者,也就是存在“被精神病”可能的患者,允许在治疗期间对于医疗机构定期复查的结果申请复诊、鉴定呢?毕竟,保护患者的人权利益当然比其他利益为高。
第二、“被精神病”患者的救济。
如前所述,“被精神病”大多情况下是有原因的,一旦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之前的纠葛很容易不了了之,这也是“被精神病”之所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目前的“草案”中,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护,见于第四条:“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享有的受教育、劳动、医疗、隐私、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以及第六十七条要求医疗机构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会见探访者等权利。这些规定虽然不够具体,但已经表明,“草案”试图建立“被精神病”患者相应的救济途径。
笔者认为,非自愿住院的精神障碍患者,除监护人代为行使相应的权利,如起诉、仲裁、申诉等以外,在治疗期间,法律应当对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基本人权做更具体的规定。如允许患者会见包括监护人在内的所有的亲朋好友,允许患者用电话、邮件等各种途径与外界沟通,开放互联网,允许申请司法救助或律师帮助等。另外,如果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认为确有必要,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独立调查。
在治疗模式上,逐步改变目前封闭式的环境,变封闭式为半开放式、社区式的医疗环境,这不仅有利于一般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更可以避免将精神病院作为限制人身自由场所的行为,让“被精神病”失去生存的基础。
第三、“被精神病”责任人的惩罚。
对于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行为,“草案”第六十七条对医疗机构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故意或者疏忽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规定了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第六十四条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二)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
也就是说,对于“被精神病”责任人,包括强制送来住院的利益冲突方以及错误诊断为精神病的医务人员及医疗机构,“草案”都主张予以严厉惩罚。
但是,遗憾的是“草案”对于“被精神病”责任人的惩罚难以具体落实。首先,如何认定故意?精神障碍的诊断须由医疗机构做出,其他人完全可以用不懂专业知识为由推脱责任,司法实践中很难认定其主观状态是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即便是医务人员,由于诊断标准难以统一,所以也很难认定其故意误诊;其次,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依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利益冲突人制造“被精神病”,侵犯了对方什么权利?人身权抑或财产权?如何赔偿?赔偿什么项目?如何计算?这些都是难解的谜题;再次,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难以找到答案,所以,要杜绝“被精神病”,对于责任人的惩罚仍需法律进一步的规定。
笔者建议,鉴于目前“被精神病”多见的原因是利益争夺、滥用公权力等,并与医疗机构沆瀣一气,共同损害“被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应当有针对性地制订惩罚性条款,特别是涉及滥用公权力的情况。只有建立有足够威慑力的惩罚制度,使得利益冲突方在制造“被精神病”后得到严厉的处罚,“被精神病”才可能不被滥用,精神病院才能真正成为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康复乐园。
行文至此,笔者仍然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什么原因“被精神病”,都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侵犯,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必须杜绝这类病态事件的发生。而且,如果“被精神病”这种恶性事件不被追究,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暴露在成为“被精神病”的危险境地,这也是精神卫生立法应当解决“被精神病”的呼声如此之高的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康昕律师事务所)
继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之后,1982年6月底和7月初,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检察分院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马振龙、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朱永嘉分别向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市高院、市中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7月至8月对案件进行了审理。
团体组织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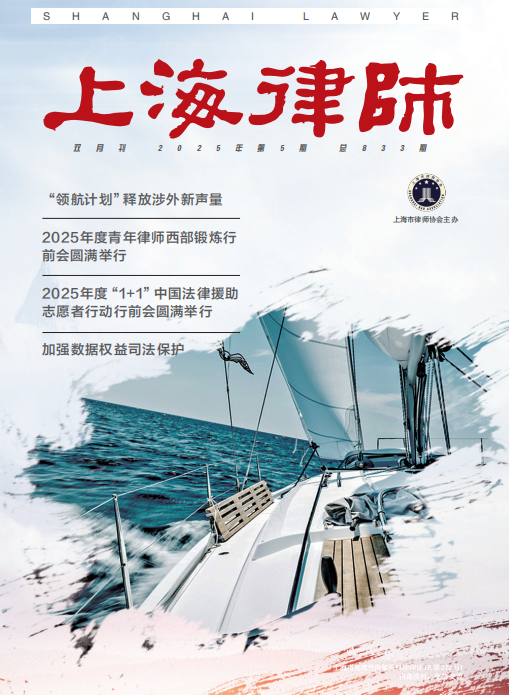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