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从一起败诉案件谈法官的“自由心证”
日期:2011-11-01 作者:连晏杰
案情介绍
杨某于2010年5月因交通意外突然死亡。杨某的妻女在万分悲痛地为杨某办完丧事后获悉,杨某生前还曾借有一笔债务。杨某生前好友白总告诉杨某妻女,杨某在出事前一年曾向白总的企业借款人民币50万元,当时其借款的理由是给女儿购房之用并说好在2009年10月底前归还。由于平时和杨某关系不错,了解杨某的经济能力和为人品行,更何况有双方共同的好朋友马先生在旁见证,白总遂同意向杨某借款。白总根据杨某的要求,开具了一张收款人为某房产公司,金额为50万元的支票给杨某。杨某在签收支票的同时,自行起草了一份借条,借条约定了借款50万元,利息按银行利息执行,2009年10月底前归还。该份借条是杨某手写,并用复写纸一式两份,写完并由杨某和白总共同签字后,杨某取走了该协议的上面一联。白总称,其在2009年10月曾催讨过该笔借款,当初杨某向其出示了一份外地房产的房产证,说自己投资了一套外地的房子正在挂牌出售,等房子卖掉了就归还欠款。白总考虑和杨某关系不错,而杨某平时也确实是言而有信的人,故未再继续催讨借款,而是等杨某出售房屋后主动还款。
由于杨某意外死亡。白总不得不请了当初的见证人马先生一起找到了杨某的妻女,并出示了全部证据。出于平时对白总和马先生的了解,杨某妻女完全相信他们说的是事实,但她们却并不知道该笔款项的去向,也不知道杨某买房需要资金一事,更不知道杨某在外地某处投资有房地产。此时,马先生告知杨某妻女,据其了解,杨某生前可能和一个郭姓女子有亲密的男女关系。杨某妻女翻看了杨某的遗物,找到了一份外地房产的房产证,房屋所有权人真是该女子郭某。但在杨某的遗物中,并未找到被杨某拿走的借条。而白总也向房产公司了解到其公司所开具支票所购房屋的地址,而根据房地产信息登记资料显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同样是郭某。据马先生称,郭某之前在娱乐场所工作,与杨某在娱乐场所结识,认识杨某以后生活应该是由杨某供养,不再继续到娱乐场所工作。对于这样的结果,杨某妻女显然无法接受,遂决定委托律师向郭某讨回这50万元。
办案手记
接手这个案件以后,我们在选择基础法律关系方面颇费了一番脑筋。首先是主体的选择,鉴于白总公司开具了支票给郭某用以购房,我们可以请求白总公司直接起诉郭某,要求返还不当得利。但我考虑到白总和郭某素不相识,很难合理解释支票为何会开具给郭某购房的房产公司,而白总和杨某签署的借条在遗物中并未找到,有可能就留存在郭某处。如果郭某届时出示该份证据证明该笔款项的支付是基于白总公司和杨某的借款合同关系,公司起诉所依据不当得利的基础法律关系便很难被认定了。因此,我们还是决定杨某妻女以杨某继承人的名义起诉郭某。此时,我们便又面临着第二个选择,究竟是以何种基础法律关系起诉?比较常见的观点包括不当得利、借款关系以及基于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并侵害女方利益。最终,我们选择了借款关系作为请求权基础。
庭审过程中,被告方律师确认了我方所主张的借款合同关系。但被告主张其已经向杨某归还了借款,证明其已经还款的证据就是杨某书写的借条上联的原件。对此,被告的解释是,被告知晓杨某借给她的50万元是向某公司所借,因此被告向杨某还款后,要求杨某立即向该公司偿还该笔借款。杨某此后告知其已经归还了该50万元,并将公司的借条原件交付给她。同时,郭某在借款时曾写过借条给杨某,但还款给杨某以后郭某收回了所写借条并销毁。至此,本案让我们较为担心的基础法律关系已经不再存有争议,并且基于借款法律关系的借款交付也没有任何疑问。案件的争议焦点集中到了一点,就是被告是否已经充分举证证明其已经向杨某归还了借款。对于这一问题,我方认为被告方显然举证不足。首先,我们认为被告出示的唯一一份证据是一份间接证据,并且在证明内容上不具有排他性。杨某完全可能是由于该笔借款是为郭某所借,因此就直接将该份借条第一联(并且从证据原件的背面来看,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该份借条还有一份复写件)转交给了被告。因此,在存有其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该份证据显然是不足以证明被告郭某的还款事实。其次,根据上海高院的相关民事法律问答,大额借款的资金交付,不能仅凭借条,甚至不能仅凭接受钱款一方的自认,需要同时审查资金的来源和走向。本案所涉还款金额为50万元,被告显然需要提供资金来源以及资金走向的证据。第三,退一步讲,鉴于本案两个借款关系的独立性,即使法院认为借条第一联原件能够证明杨某已经向公司归还了借款,并不能由此推得被告已经将钱款还给了杨某。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告方还向法庭提出两点请求。第一,希望法庭能够调查郭某所购房屋首付款中除50万元以外其他款项的支付来源,因为被告的预售合同显示,其首付款除50万元支票外还应支付10余万元,原告推测该10余万元很可能是杨某的拉卡消费(由于原告并不掌握该部分证据,且律师持调查令调查被房产公司拒绝)。第二,我们希望被告能够提供其还款资金的来源。因为被告系20多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证登记的工作为菜市场营业员,50万元于她而言并非一笔小数目。针对原告的第一个请求,法院以和案件没有关联予以拒绝。针对第二个请求,被告方则提供了两份手写的借条,证明其还款资金来源于向他人的借款。对此,原告认为出具该两份借条的借款人应当作为证人出庭。在证人出庭的基础上,原告希望征询出借人的出借资金来源,其与被告关系以及借款动机等一系列问题。遗憾的是,证人并未能出庭。且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郭某本人也从未出庭。
最终,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判决认为被告郭某持有杨某手写借条符合一般借贷和还款的惯例,并且郭某对持有该借条书写件解释为是杨某交给她作为欠款了结的凭证,该解释符合一般常理。甚至被告作为证明其资金来源的借条都未在判决书及判决理由中涉及。
一审判决后,原告提出了上诉。并且原告在上诉期间,在杨某的电脑中找到了和被告共同去海南旅游所拍摄的照片并在二审中作为新的证据提供,原告认为基于原被告的特殊关系,原告不要求被告书写借条,并且原告将写给公司的借条第一联存放在被告处都存有较大可能性。同时,原告书面向法院申请被告本人出庭以便于查明事实。遗憾的是,我们的二审法院秉承着我们并不陌生的,凡是没有重大相反证据证明即“将错就错”的办案作风,驳回了原告的上诉。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二审法院就一审都不敢认定的两份借条(无证人到庭,无资金来源,甚至借款人是否客观存在都无法确定)予以认可,并据此作为认定被告资金来源的唯一证据。
案后感悟
自由心证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through inner conviction)源于“罗马法”,是指一切诉讼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法律预先不作规定,而由法官、陪审官根据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称为心证。心证如果达到深信不疑的程度,即谓之“确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法官审判案件只根据他自己的心证来认定案件事实。
自由心证制度要求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合理判断证据的证明价值。自由心证制度已成为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普遍的证据原则。在我国,尽管在《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并未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客观存在和普遍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也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其实是对关于法官自由心证的一种确认。
在本案中,被告对于还款一节事实进行了一定的但又不完全充分的举证。这其实就依赖于法官通过“自由心证”来衡量证据对待证据事实的证明力。结合本案的情况,我们很想用一系列的问题去问被告和证人,来帮助法官形成正确的内心确信,可惜我们并不是以律师为庭审主导的英美法国家。我们相信,具有社会普遍认知水准和社会经验的人们应该能够判断清楚本案的真实事实,可惜我们并没有陪审团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法官就更应该去查明一些“周边事实”来形成他们的“内心确信”。比如,被告剩余房款的支付情况,被告的真实经济状况,借钱给被告的“债主”钱从何来为何又愿意借给被告,甚至是被告与杨某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调查结果可能甚至是对被告有利的,但这些问题的核实至少能够让我们理解法官形成“心证”、“内心确信”的“心路历程”。“自由心证”赋予法官至高的权力,法官应当无比慎重并真正忠于内心地去使用“它”,“自由心证”其实并不“自由”。
我以为,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需要更多一点对“自由心证”的约束,尤其是二审法院,不要一旦原审判决所依据的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二审便一味地予以维持。在法官素养方面,当需要面对“自由心证”的时刻,请更多一份慎重和真正的忠于内心。这样才能实现对当事人的公平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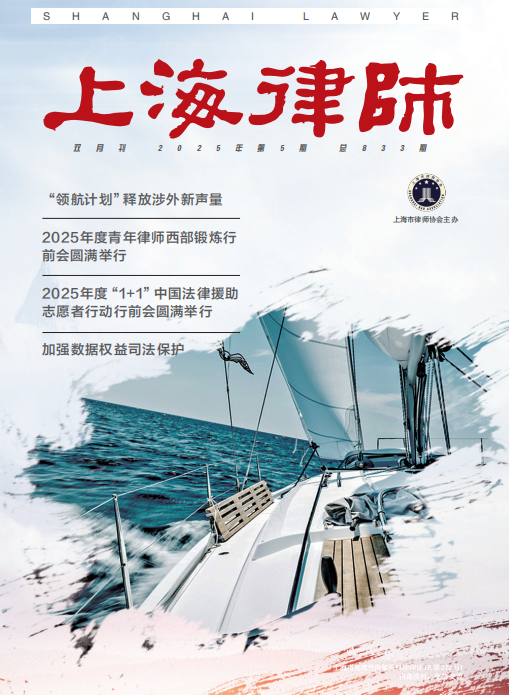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