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不动产盗窃行为无法入罪 民刑法律冲突效果负面
日期:2012-10-08 作者:陈浩榕
随着社会经济及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不动产盗窃行为无法入罪这一情况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已日益凸显,笔者以自己代理的一起案例为样本来作些剖析。
一、案件判决凸显法律尴尬
龚某名下有一套位于本市浦东新区的房屋,登记的产权人为龚某一人。2008年,龚某之子伙同朋友丁某窃取龚某的户口簿,然后利用龚某的户口簿,以挂失龚某身份证的方式重新领取了龚某的身份证,又以挂失的方式领取了龚某的房产证。随后龚谋之子冒充龚某,与丁某一起至公证处办理了委托丁某出售房屋的公证委托书。至此,龚谋之子及丁某获得了出售龚某房屋所需的全部材料,即:龚某户口簿原件、身份证原件、房产证原件及公正委托书原件。
而后,龚某之子及丁某将房屋委托中介挂牌出售。买受人王某通过中介看到该房屋的出售信息后,即通过中介与丁某取得了联系。王某审查了龚某的户口簿、身份证、房产证及公证委托书原件,并亲自至房屋内查看,房屋内当时系由一租客居住。
王某按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了全部房款,而后丁某将该房屋过户至王某名下。
龚某之子及丁某取得房款后均用于归还赌债。后因王某与龚某联系租客租金事宜,龚某发现房屋已被出售。龚某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法院起诉王某,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龚某之子及丁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以合同诈骗罪于2010年4月被定罪,刑事判决书同时认定王某为合同诈骗案的被害人。龚某起诉王某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案,一审法院于2011年9月判决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且王某不适用善意取得,应涤除房屋贷款后向龚某返还房屋。
当龚某向法院起诉买受人王某要求认定房产买卖合同无效后,王某委托笔者作为本案代理人。笔者接受委托后,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即向法庭提出了丁某的行为属于表见代理及王某属于善意取得的代理意见。但就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后,丁某及龚某之子被公安机关抓获,本案也因该刑事案件而中止审理。
在刑事案件作出前述一审判决后,本案即恢复审理,龚某将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书作为新增证据向法庭提交,并主张基于该刑事判决认为王某系刑事案件被害人,故房产买卖合同无效。而笔者作为王某代理人虽在之后的庭审中向法庭提供了包括证人出庭作证形式在内的大量证据用以证实王某的整个买房过程已充分尽到了审慎义务且无任何过错,故应属于善意取得,但法庭最终还是认定因丁某的行为属于刑事犯罪,故本案不适用善意取得,并由此作出买卖合同无效的判决结果。
二、民刑冲突导致把握失衡
基于以上的案情及判决,我们不禁要问:王某为何不能依据善意取得获得房屋呢?根据《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受让人只要符合“受让的善意”、“合理的价格”及“合法的登记”这三个要件,就可以认定善意取得不动产。但本案中法院又为何没有适用该条法律规定呢?细想之下可发现,由于刑事判决在时间上先于民事判决,导致了民事判决根本无法再适用《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法律条款。
首先,由于刑事判决认定王某为合同诈骗案的被害人,并要求龚某之子及丁某向王某返还赃款。这一判决实质上已经认定王某因未取得房屋,所以遭受了财产损失。而王某为何没有取得房屋,刑事判决没有说明,实质上也无法进行说明。
从合同诈骗案被害人的特征来看,一定是在犯罪行为中遭受实际财产损失的。如未遭受实际损失,则只能说明其在犯罪过程中“被骗”,而非“被害”。这是在诈骗类犯罪中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么本案中的王某是否遭受了实际损失呢?要判定王某是否遭受损失应当依据民事法律而非刑事法律。《物权法》第106条就是判定王某没有遭受损失的最好依据。但遗憾的是,刑事判决并未能考虑《物权法》关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而是简单地认定王某因为被骗取了购房款而遭受了损失,进而认定王某为合同诈骗案的被害人。
其次,如再细究,我们可发现,龚某之子及丁某两人的行为其实属于典型的不动产盗窃行为,而正是因为不动产的盗窃行为无法定罪入刑,从而导致了刑事判决只能认定龚某之子及丁某构成合同诈骗罪,否则龚某之子及丁某两人将面临无法定罪的尴尬局面。既然只能认定两人构成合同诈骗罪,那么自然也就只有王某能被认定为被害人了。而民事判决正是受到了刑事判决认定的影响,无法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一旦民事判决再适用了善意取得,则将非常明显地与刑事判决相矛盾,如判决认定王某因善意取得已获得房屋所有权则意味着王某并未遭受损失,遭受实际损失的将是龚某,这将对刑事判决结果造成根本性及颠覆性的影响。
三、司法缺陷带来负面效应
有人提出法院不适用善意取得可能是基于丁某并非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代理权,故不符合善意取得理论中的无处分权人,笔者对此不能认同。实践中对无处分权人确实有相应理解,一般指:承租人、保管人、共有人、代理人等。但这些理解主要是基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而产生的,本案中丁某是否通过合法方式取得代理权并不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定要件。且笔者以为,当法律理论解释法条时,关键在于符合该法条的立法本意。而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质在于保护无过错第三方的交易安全。
纵观全案,上述刑民法律及判决上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迁就并非是因为在该领域缺乏相应的成文法律,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刑事司法实践在不动产盗窃方面的空白以及对于《物权法》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必要的指导所致。而这样的法律冲突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将是非常巨大的。
第一,本案的民事判决实质上否认了《物权法》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有效性,其对于成文法适用的否认,必然影响全社会对法律指导及评价作用的认识,从而影响法律在社会中的公信力。
第二,本案的民事判决将对整个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安全性带来极大的冲击。目前,有很大一部分的房产交易是通过委托代理人进行的。而经过公证的委托书是买受人判断代理人真实性的最重要的依据。本案的民事判决彻底打破了这最重要的可信依据,从而使得日后的房地产交易市场无任何安全性可言,即使是与产权人本人交易,亦将面临产权人本人被他人冒充的巨大风险。
第三,本案的民事判决将造成对各方义务及责任分配的不公平及不合理。就本案来看,龚某及王某确实都是无辜的受害方。但从自身义务的角度来看,王某在整个购房过程中已经穷尽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所有的可行的合法行为及义务。而龚某是否又穷尽了所有能保护其财产安全的行为及义务呢?当然,我们不能苛责任何一方是否存在过失。但从对比两方所尽的义务及所需承担的责任可看出,本案的民事判决确实存在不公平及不合理之处。
四、解决之道其实有章可循
本案确实是民刑法律冲突所导致的一个典型案例,而造成这一切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不动产的盗窃行为无法入罪。在刑法理论上对于不动产盗窃的争论也屡见不鲜。那么,不动产盗窃行为入罪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之下是完全可行的,以下从两个方面作一简要论述:
第一,如何确定不动产盗窃的既遂、未遂与犯罪预备。
目前刑法理论通认的盗窃既遂认定是“失控说”加“控制说”。即盗窃行为人实际控制了财产,而被害人实际失去了对财产的控制。那么,对于不动产盗窃而言,又如何认定“失控”与“控制”呢?
笔者以为,由于不动产不可移动性这一有别于其他动产类财产的特性,因此,将产权登记是否变更作为被害人是否失控是具有合理性的。一旦被害人名下的房产登记因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被变更,则可认定被害人已对不动产“失控”。而行为人能将被害人的不动产权利登记进行变更,即可视为其已“控制”了不动产。虽然这一“控制”有别于其他盗窃中对财产的控制,不具有持续性,而具有瞬时性。但以此作为认定“控制”的依据同样具有合理性。因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的权利以登记为准,故将是否进行变更登记作为确认犯罪是否既遂具有法律依据及合理性。
由此而及,如果行为人已取得变更不动产权利人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及要件,但尚未办理变更登记,则可认定为犯罪未遂;如行为人尚在准备变更不动产权利人所需的材料,则可视为犯罪预备。
第二,认定不动产盗窃,是否会对社会公众的安全性造成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动产可以盗窃,则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产生不安全的恐慌,因为不知何时自己住的房子就会被偷了。加之现在房产价值极高,房产被盗可能会对个人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造成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但笔者以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及作用在于公平地保护全体社会公众,如果认定不动产盗窃可能引起对权利人的风险,那么,因为不认定不动产盗窃而引起的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否定就会引发对房屋买受人的风险,就如本案中的王某。
再者,认定犯罪行为的目的并非是要对公众造成风险,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众,能够有法可依地切实、公平地保护每一名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明确相应的法律规定后,可以更有效地加强各个相关部门的监管及责任,如公证处、房产登记机关,从而真正促进法律对每个公民的公平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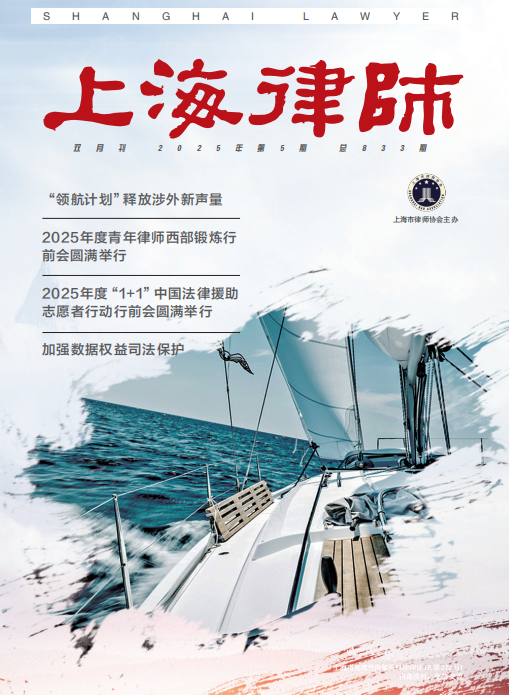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