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动态
戏曲艺术版权认定和保护
日期:2012-03-22 作者:朱小苏
在法律工作之余,笔者酷爱脸谱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痴而不讳。原以为法律与戏曲交集不多,不想近日笔者的一家法律顾问单位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某赵姓画家委托签发的律师函,责其在制作的一档戏曲类节目的片头部分擅自使用了多幅由赵某独立创作并收录在1992年出版的《京剧脸谱》一书中的京剧脸谱,侵犯了赵某的著作权,要求该单位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正当庆幸逮住这难得的爱好与工作结合的机会,意欲大干一场之时,当事人单位却告知,经粗略网络检索,数年间赵某已经打了数十场关于京剧脸谱著作权侵权的官司,其中多数胜诉,获赔数额不下数十万,故不愿做“无谓抵抗”。最终经双方协商,该案以该单位支付以万元计的费用结案。纠纷虽然得以解决,但由此延伸出的某些戏曲艺术的版权话题,却值得思考和探讨。从法律层面而言,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明确了只有具备“独创性”的作品,才能构成《著作权法》下的“作品”并受到保护,但在京剧脸谱版权纠纷中,什么才构成某幅脸谱作品的“独创性”却着实是个难题。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界定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但并没有对“独创性”的定义和客观判断标准做出明确规定,这个“模糊区”导致了实践中司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尺度不一,甚至出现了如郑成思教授所言的“在认定或否定侵权的过程中,原地踏步,乃至扩大模糊区”的情况。从另一个角度,京剧脸谱属于民间艺术的特性也增加了认定其“独创性”的难度。根据英美法系国家判例中出现、并经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法学者肯定的“三步侵权认定法”,把不属于特定权利人版权覆盖范围内的他人、前人的成果“过滤”出去的步骤对判定“独创性”至关重要。然而,作为我国戏曲艺术中特有的一种造型手段,脸谱与唱腔、表演、服装等其他技艺一样,随着中国戏曲艺术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形成。在延绵至今的成百上千年中,虽有革新和创造,但更有前后相承的关系,恰如京剧名宿刘曾复教授所说,“脸谱的不同风格、流派……衣钵相传,影响后世,科班学生的脸谱各有师承和风格……传流至今,对今天京剧净角脸谱的定型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如此漫长而又具体的演变过程中,怎样将某幅作品中自有的“独创性”从前辈作品中抽丝剥茧地脱离出来,应是争议问题的关键。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有关脸谱版权纠纷的判决文书对该点的分析都似蜻蜓点水,不着重墨。
就赵某的个案而言,在笔者看到的有限的判决书篇幅中,似乎将赵某作品的“独创性”归纳为:1、脸谱使用工笔正面画法,具有无头饰和髯口、人物端庄、着色自然等特点;2、线条、笔锋、构成图案的分布位置等勾脸技法上不同于别人。针对这两点,笔者个人以为尚待商榷。关于脸谱正面画法,笔者见识粗浅,但似乎并非赵先生原创,前辈京剧大师已多有采用这种正面的、不加头饰的、不戴髯口的脸谱画法。在看到的一本出版于1968年的名为《听雨楼脸谱》的京剧脸谱集中,绘制的脸谱即为正面画法;同好告知,1990年田兆霖先生出版的《京剧脸谱集》里绘制的200余幅脸谱也为正面图,这些作品皆早于赵先生《京剧脸谱》的出版时间。而就勾法上的独创,笔者并非专业戏曲人士,更不敢妄评,但在分析该问题时,无法也不应脱离京剧“程式化”的核心特点去考虑。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曾言:“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这三个基本特征是京剧界经过多年探讨积累了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概括而成的。”而脸谱作为戏曲的化妆方式,一笔一划也应总在方圆之中,遵循既定的色彩和谱式,这是脸谱的本质功效——区分人物所客观决定的。这套经过历代艺人长期生活体验和艺术创造所形成的独特格式,已经赢得了观众的接受和认可,在此基础上任何勾法的创新,也不能超脱其原有固化的谱式,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就脸谱的固有谱式,更接近版权保护中的“惟一表达”原则,即如果某一客观事物,只有一种表达方式,则这种表达将不被认为具有“独创性”。这点上,笔者倒是更赞同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国忠在赵某与某出版社出版的《戏曲年画与脸谱》版权纠纷一案中的审判观点,即“京剧脸谱是京剧艺术家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对特定戏剧历史人物面部特征的描述,是具有程式化且与戏剧历史人物具有唯一对应性的表现方式。任何人绘制京剧脸谱都应采用同一标准,否则将造成历史人物识别上的混乱,这是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原告赵某绘制的京剧脸谱只是对戏剧舞台上的历史人物面部特征的复制,并不因此享有对该京剧脸谱的著作权。”
除去“独创性”本身的认定值得推敲外,在此类京剧脸谱或其他戏曲艺术纠纷中,如何营造一个更公平的审判程序,似乎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众所周知,作为民事部门法中的一门,《著作权法》也旨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此处的“平等”强调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平等。笔者在此对赵某提起的众多版权纠纷案中当事人法律人格的平等性并不存疑,但他们在民事诉讼中是否真正形成均势却打着问号。理论界认为,“只有在有关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均势,即他们实现权利的能力大体相同时,才能期待每一方当事人都能在自由交易中实现自己的意志”。案件一方的赵某“5岁开始学习绘画,尤其喜欢戏剧人物和京剧脸谱,多年来几乎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研究京剧脸谱上”;而另一方(包括其聘请的律师在内)绝大多数都并不拥有太多的脸谱或戏曲专业知识,处于绝对的弱势。这样的双方在诉讼程序中,难免导致案件向强势者单方面意志表达的方向发展。在此情况下,法官有义务发挥司法能动性,因势利导,通过一定方式平衡双方的力量,例如引入第三方通过专业鉴定确定“独创性”是否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指出,鉴定应当是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故鉴定结论是法官对案件事实认定手段的延长,鉴定人是法官或法院的助手,法官借助鉴定结论来认识案件事实的真相。可惜的是,在笔者看到的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文书中,没有一家法院在脸谱比对中引入司法鉴定。当然,由于我国采用鉴定人登记管理制度,可能也没有任何的戏曲专业人士登记申请成为此类案件的专业鉴定人士,所以也怪不得法官。但由此造成的尴尬局面就是审判人员本身无法通晓博大精深的戏曲专业知识,又无法如其他案件那样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盲目断案,依照明文授受、机械执法也就在所难免。
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分析,翻看可以查阅的判决书,在所有案件审理中,审判法官一方面都将京剧脸谱视为《著作权法》下的“美术作品”加以保护,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否认脸谱于一般美术作品的与众不同,即其并不具备一般著作权作品所拥有的明显特征。以“独创性”为例,《著作权法》通常要求作品必须是作者独创,而不是在公共领域已经存在的作品,而脸谱恰是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艺术形式,通过代代相传逐渐演化形成,并且一直在公共领域流传着,根本而言,其无法满足《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要求。因此,包括脸谱在内的戏曲艺术从本质上更接近“民间艺术”。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审议并通过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免被滥用国内立法示范条款》,“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已经从传统著作权法中独立出来,以专门的法律进行保护,而在我国的国内立法层面,该种“民间艺术”仍被纳入《著作权法》的体系中,冠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名加以保护,但法条仅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这样的草草规定,究竟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立法者时至如今也没有想清楚,国务院迄今也没有颁布具体的保护办法。如题述京剧脸谱这类民间文学艺术基础上再创作的作品的认定及保护的问题,其实类似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修改权”或“改编权”的权利授予问题,但正由于我国在此立法领域的留白,虽涉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纠纷不断涌现,此类问题仍只能窠臼于《著作权法》的规定加以处理,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在赵某的脸谱诉讼案中,许多被告已经指出赵某的行为有“圈地”之嫌,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借诉讼占为己有,并利用其牟利。对这样的指控是否成立,笔者不想多作评判,但如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瑰宝,在宽容和保护中取得平衡,确实是个时不我待的话题。好在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已经将民间文学艺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2011年的调研课题,相信有关司法解释将进一步出台,以弥补此空白。
最后,跳出法律层面,京剧脸谱的版权纠纷其实仅是戏曲艺术著作权保护话题中的一颗小水滴(请原谅笔者在此使用“戏曲艺术”而非《著作权法》下的“戏剧作品”概念,因为法条规定的“戏剧作品”定义为“话剧、歌剧、地方戏等供舞台演出的作品”,并未囊括京昆这样的全国性剧种;更何况,笔者看来,“戏曲艺术”也远非法条通常指向的剧本所能尽揽)。记得笔者在多年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呼吁不应过分在当下的戏曲界树立太强的版权意识,其原因主要在于:一则由于特殊的生存环境,戏曲界素有“偷戏”的旧习和“私淑”的传统;二则在目前戏曲不景气的环境下强调版权意识将阻挠剧目的移植或流传,反而成为戏曲传承发展的绊脚石。今日回顾来看,当时观点的阐述或不全面。确切地来说,版权分为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笔者并不反对戏曲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权利人的精神权利(如署名权、发表权等)进行保护,因为它属于人身性的专属权利,不加维护则难以鼓励创作,但前提必须是确有充足的证据和资源使得我们可以去溯源归真,而不是滥打版权官司,搅得戏曲界再无宁日。而对于版权下的财产权利,尤其是在流转中的经济收益或“付酬权”,笔者仍然认为在现今不宜过分强调。换个角度,肯定有人会质疑这样的举措扼杀了物质激励,会损伤权利人的积极性。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但这可能更需要政府从创作源头上给予资金扶持和奖励,此乃是无奈而现实之举。
西方的法哲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其经典著作《法律:实现目的的手段》中指出,任何法律均有其目的性,目的是整个法律的创造者,而法律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一项法律的立或废均应以为其期待实现的目的服务,而执法和司法也不应仅为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容,而应实现法律的社会效果。据笔者所知,荷兰为了鼓励本国企业飞利浦做大做强,曾将《专利法》的出台时间延缓了近二十年,以便提供其足够的时间免费拷贝别国的专利累积资本;我国的《反垄断法》从草案到颁布历时十三年,一项重要的原因也恰是出于扶持民族企业发展之考虑;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在其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其实施力度更会随社会经济的繁荣或萧条而或严格或宽松。
回到戏曲艺术这个主题,毫无疑问,每部戏曲剧目的创排演出都将投入不菲的成本,若过分强调版权的经济利益,剧目的流转传承、表演的借鉴移植都将背负高额的版税,无疑将使前进的每一步都迈得举步维艰,这也与《著作权法》激励创新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前些年,上海京剧院曾以1元钱作为版税,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之一《廉吏于成龙》的剧本版权许可给山西省吕梁市晋剧院和青年晋剧团,恰是为如何在现今社会行使和尊重版权树立了一个典范。鉴于目前戏曲市场处在低谷,或许看淡版权的收益从而“放水养鱼”,让越来越多的人从认知上对其接受和欣赏并逐渐参与其中,可能更有益于戏曲这门民族艺术的市场培养和演出繁荣。当然,这是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笔者愿与同仁就此商榷,以求雅正。●
(作者单位: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
团体组织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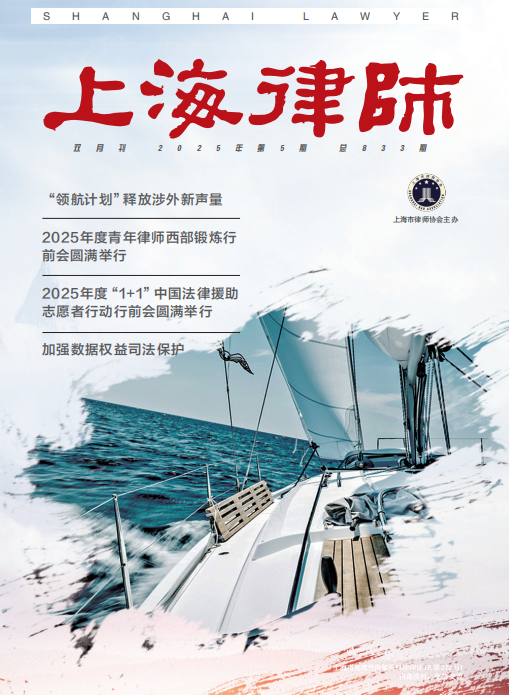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