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
为了让更多人受到法律援助 申城律师力促《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立法侧记
日期:2006-07-07 作者:党文俊 阅读:3,380次
2006年7月1日,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正式实行。法律援助,这个被社会学家定义为“衡量社会和谐度标尺”的名词,在上海被赋予了新的“法律内涵”。这也是上海地方立法史上,第一个由律师“主推”的立法工程。去年7月,市律协法律援助与社区服务研究会成立,今年7月,由上海律师主推的《若干规定》又应势出台。在法律援助这个舞台上,上海律师正踏着《若干规定》的新节拍,跳出更精彩的舞步。
缘起:法律援助“难援”救人英雄
11年前,1995年的夏天,陈先生舍己救人,把两个玩耍的小孩从即将倾倒的墙下推开,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双腿。“救人英雄”的光环,随着时间的流逝,趋于黯淡。面对高额的医疗费,面对今后失去基本工作能力的生活,谁对见义勇为的英雄伸出援手?
当年为陈先生追讨医药费和生活费的,正是上海市人大代表、四维律师事务所主任厉明律师。“由于墙体倒塌的肇事货车所属的运输公司不肯赔付,维权必须对簿公堂!但在为陈先生申请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由于见义勇为在当时并不是法律援助的“法定事项”,在申请法律援助时,陈先生仍须接受与常人同样的经济状况审核。
按陈先生当时的经济状况,要略高于受助标准,在各方面的协调下,陈先生才“破格”纳入了法援的对象。打赢了官司,陈先生从运输公司获赔了30多万元。
救人英雄险些被法律援助“拒之门外”。厉明深刻地体会到,法律援助规范的不完善,阻碍了“让更多‘有理无钱’的公民得到法律救济”的法援精神的实现。
厉明指出:“很多见义勇为者的经济状况可能都要比法律援助的标准要高,但我们的社会怎么忍心见义勇为者,在义举之后,还要为维权再掏出一笔律师费?”
进程:律师率先起草立法蓝本
在2003年的“两会”上,厉明递交了“建议制定《上海市法律援助条例》”的议案,一系列的建议中包括将“见义勇为者”列入上海法律援助的“法定受助对象”,这也是上海律师界为法律援助事业立法,发出的第一次呼喊。
2005年7月,以厉明的这份议案为蓝本,形成的《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正式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提请人大审议。在这份草案中,详细规范了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和经费保障等内容,对上海市19个区县的20个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
厉明的立法呼吁,得到了同样是律师界市人大代表的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徐晓青的积极呼应。
徐晓青的另一个身份是上海市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社区服务研究委员会主任,他与研究委员会的“主力干将”岳文辉律师、毛国平律师、曾清律师一起,围绕“上海律师参与法律援助”展开了深入调研。
他们的第一个成果是完成了司法部指定由市法律援助中心起草的《法律援助服务人员行为规范》。
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徐晓青代表提交了《关于〈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的书面意见》。
这份书面意见针对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等提出的全面的数据分析与详实的立法意见,也成为了此后立法听证会上讨论的重点文件之一。
同样在今年的“两会”上,厉明又趁势提出了关于制定《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的配套规定》的议案,希望能进一步有效规范社会组织和个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行为,为法援立法继续造势。
调查的结论是,市律协每年义务承办的困难群众援助案件远高于同期办理的标准法律援助案件,老的法援标准“脱离”法援现状。
听证:建议降低援助准入门槛
今年2月24日,上海市人大法制委会同市府法治办召开了由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等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参加的《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立法听证会,市人大代表徐晓青、厉明以立法提案者的身份出席。“法律援助如何泽惠黎民百姓?确定正确的法律援助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至关重要!”听政会上,两位律师代表的发言得到了相关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很多意见直接被立法部门采纳。
徐晓青在听证会上指出,根据《2003上海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中,可支配收入低于其消费支出的最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人数之和,占本市人口总数的15%,远超过最低生活保护线所覆盖的45%的比例。“若按照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法援标准,实际上将一部分应该获得法律援助的人群挡在了法律援助大门之外。”
亮点:律师介入法援有法可依
对于新出台的《若干规定》,两位律师人大代表都给予了积极评价。徐晓青认为,新的规定基本符合上海法律援助工作的现实状况,“这是市人大开门立法、民主立法下,诞生的一部比较成功的法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今后律师介入法援工作将有法可依。”
厉明将《若干规定》的出台,定义为“我国公民权利保护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在过去,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不同,司法救济尚不被列入政府认可的基本生活保障范围中。新的《若干规定》将见义勇为纳入援助范围、降低了法援对象的进入门槛,实际上都代表了一种趋势,即把司法救济消费纳入了公民必需品的范围内,这是法治文明进步的体现。”
业内热点
法治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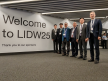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沪公网安备 31010402007129号
